荆楚网 楚天都市报
文/通讯员 范宁 记者 王予 摄影/迪戈
我们的城市正在不断的扩张。高楼的林立,住宅小区的出现,私家车的飞速发展,网络社会的魔幻……空间、速度、时间的改变,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儿时记忆中,街坊邻居互相串门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悠悠泡一杯茶踱着方步与客人周旋的场景,在我们的视线中越来越稀有。
然而,在一些老城区,仍然有这样一些地方,它们固执地拒绝着时光的改变,顽强地保留着几十年前的生活风貌……
[寻访]黄昏行走
我们寻访这家旧称“车站理发店”的小店时已近黄昏,天空渐渐有了一层暮色。理发店夹在汉口老火车站前两排陈旧黝黑的五金、小吃铺当中,看起来并不显眼———就是寻常街道寻常人家中的寻常小店。
店子向内纵深了二十来个平方,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造型:老式推子,折叠剃刀,笨重的可升降座椅,黄色的木抽屉,还有套着白大褂盖着毛巾睡觉的伙计。
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生意很清淡,店里没有什么顾客,只有一位等着修面的先生。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滞了,我们好像又回到了记忆中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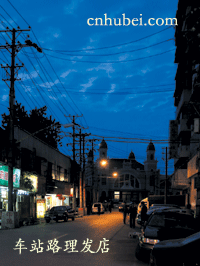 车站路理发店,就在离老汉口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照片中那团光晕的下方。它掩映在这样的夜色下,和这条路,这座火车站,融为了一体。
车站路理发店,就在离老汉口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照片中那团光晕的下方。它掩映在这样的夜色下,和这条路,这座火车站,融为了一体。
[怀想]历史烟云
这里的人们,把租界风云变迁的隐痛埋在了心里,过着自己或平凡或动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一个地方,把这些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联系到了一起。就是这家小理发店,靠近法租界,离汉口老火车站不远。它曾经迎接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至今还保持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质朴的面貌。
它慵懒缓慢的节奏,让我们想起旧时的生活,它们在五光十色的都市中已经失传很久,却在这里倔强地生存着。我们有些疑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这种生活方式,从不曾被现代城市所改变?[溯源]前世今生
车站路以汉口老火车站为起点,一直延伸到江边“邦克街码头”,其中大部分在1896-1943年间是法租界。作为汉口铁路和水运的枢纽要冲,车站路是商贸中心的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汇集了大量人员的流动,服务业也随之兴旺。旅馆饭店遍布四周,贩夫走卒摩肩接踵,加上发迹于此的富商巨贾,定居于此的外国移民,造就了车站路昌盛的景象,也给那担着挑子随街吆喝的剃头匠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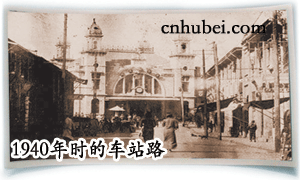 车站路理发店,现在仍是集体企业,现在的负责人姓易,年龄大约有40多岁,在店里呆了20多年。据易经理回忆,理发店在解放前就有了,最初是由剃头挑子发展而来的,客人大多是南来北往的乘客,以及引车卖浆的小摊小贩和一般市民。至于老板最处的是谁,有何轶事?已经无据可考。那时的车站路地貌与现在没什么区别,人们就坐在街边剃头,捂着热毛巾修面,和来往的街坊打个招呼。解放后,和其它手工业一样,剃头匠们走进了店铺,做起了集体所有制理发店的师傅。由于汉口火车站的存在,车站路人流如织、商业发达,理发店的生意也很是兴旺。随着老火车站的迁走和新潮理发店的兴起,理发店的生意越来越差。
车站路理发店,现在仍是集体企业,现在的负责人姓易,年龄大约有40多岁,在店里呆了20多年。据易经理回忆,理发店在解放前就有了,最初是由剃头挑子发展而来的,客人大多是南来北往的乘客,以及引车卖浆的小摊小贩和一般市民。至于老板最处的是谁,有何轶事?已经无据可考。那时的车站路地貌与现在没什么区别,人们就坐在街边剃头,捂着热毛巾修面,和来往的街坊打个招呼。解放后,和其它手工业一样,剃头匠们走进了店铺,做起了集体所有制理发店的师傅。由于汉口火车站的存在,车站路人流如织、商业发达,理发店的生意也很是兴旺。随着老火车站的迁走和新潮理发店的兴起,理发店的生意越来越差。
易向我们描述了往昔顾客盈门的盛况和那些匮乏岁月单纯的乐趣:“七十年代前,店里没有风扇;为了消暑,那时的‘风扇’就是把一块长布悬挂在理发店间,专门的伙计用力拉动,然后就形成了凉风!”
[现状]静静守望
 随着1992年汉口火车站新址奠定、整体搬迁,车站路结束了百年地利,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车站路理发店也因人流骤减,渐渐冷清下去。上世纪90年代,各种新潮美发厅出现在城市中。在那些播放着流行音乐、提供各种新奇染发烫发的发廊比较之下,车站理发店苍老的面容相形见绌。直到现在,这里剪头仍只要4元钱,修面2元钱。
随着1992年汉口火车站新址奠定、整体搬迁,车站路结束了百年地利,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车站路理发店也因人流骤减,渐渐冷清下去。上世纪90年代,各种新潮美发厅出现在城市中。在那些播放着流行音乐、提供各种新奇染发烫发的发廊比较之下,车站理发店苍老的面容相形见绌。直到现在,这里剪头仍只要4元钱,修面2元钱。
我们注意到,理发店衰旧的老墙上新挂了一块招牌,写着“车站路美发厅”。从“理发”到“美发”,从招牌由旧而新,我们可以窥见它追随时尚的艰难和无奈。
[怀想]半世城缘
 采访中,不时会有附近的居民背着手进来看热闹,理发店仿佛是他们随意出入休闲的场所,不用在乎是否打扰了生意;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并不急着去招呼他们,只用眼神打个招呼。还有搬走的街坊专程赶到店里修面:“现在的新发廊,没有剃刀,没有这里修得好,也没有这里便宜!”
采访中,不时会有附近的居民背着手进来看热闹,理发店仿佛是他们随意出入休闲的场所,不用在乎是否打扰了生意;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并不急着去招呼他们,只用眼神打个招呼。还有搬走的街坊专程赶到店里修面:“现在的新发廊,没有剃刀,没有这里修得好,也没有这里便宜!”
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看到了理发店在岁月的销蚀和市场冲击下,却依然支撑的力量。
这是一间属于整个街道整片居民的理发店,它的节奏和周围的生活保持一致,它的面貌让周围的人们感到了亲切自然,它是老武汉们用以怀旧的场所,是街坊的力量维持了它质朴的经营。而正是这种风貌理发店的存在,这里的居民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被激烈、紧张的城市节奏冲击。理发店是一个象征,它还在,那么生活还可以按原来的方式进行下去,就像人们还是在用推子而不是新式理发器具剃头一样。一家店,一群人,一段时光,相濡以沫。
………………
城市因为有人而显得气韵非凡——不敢想像,一座空城会是怎样的苍凉。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都有一段故事,一段不解的情缘。
城市偶尔的回忆
 受访人:吴明堂 武汉地方志办编纂处编辑、《汉口租界志》主要作者。1995年到武汉市地方志办工作,从此开始近十年的对武汉地方历史的研究。
受访人:吴明堂 武汉地方志办编纂处编辑、《汉口租界志》主要作者。1995年到武汉市地方志办工作,从此开始近十年的对武汉地方历史的研究。
问:“车站理发店”历经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依然能相对完整地保留着过去的风貌,其中的奥秘何在?
吴:应该是与火车站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民风民俗,有一定的关联。
有火车站的地方,就会出现大片的旅店、餐馆,就会有挑夫、摆摊等做小生意者聚集。这一点,我们在武昌、新汉口火车站以及许多城市都能感受到。尽管老汉口火车站1992年搬离了车站路,但它过去所造就出的市井形态,不可能马上消失。这种市井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这是生存的需要。
此外,这里剪头修面不过三四元钱,价格便宜;又与老街坊的情感丝丝相连,便宜和怀旧,使得这家理发店就这样不紧不慢、几乎不改原样地生存下来。。
问:新的城市文明,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您怎样评价车站理发店这种“过时”的生活形态?
吴:历史文化的传承,不光是文字,更需要实物。过去的生活形态,也是一种文化。我并不主张背离城市发展的规律,全部保留它,但至少也要留几处地方,作为“标本”保存起来。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漂亮,却和我们越来越疏离。但是这些地方,童年就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和我们的情感天然相连。
我自己就住在车站路三德里。一到夏天,这里的居民就会搬出小板凳,一家人围坐在外面吃饭。街坊邻居之间互相打招呼,家长里短地问候。到了夜晚,社区里还有拿着铜锣打更的人,一声“防火防盗”的吆喝,回荡在悠长的里弄里,特别有韵味。这种感觉让我着迷,也是在新兴的城市社区里看不到的。
没有回忆的人生是苍白的,单薄的。没有回忆的城市,同样也是苍白的,单薄的。我们的城市,不能没有回忆。
………………
江城理发店老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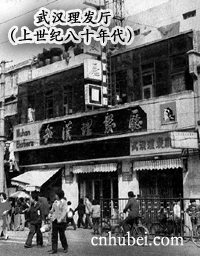 理发,是头顶大事,也是生活必需。谁没有去过理发店呢?于是,这些江城老字号理发店,成为了我们记忆中的经典。
理发,是头顶大事,也是生活必需。谁没有去过理发店呢?于是,这些江城老字号理发店,成为了我们记忆中的经典。
长生堂理发厅:创立于1911年,位于车站路,与“车站理发店”隔街相望。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者上官云珠的发型样式,即是长生堂师傅的首创。因地处法租界,顾客过去多为达官贵人、军政界要人,英国水兵来此也较多。汉剧大师陈伯华尤喜此店,前些年因病住院后仍请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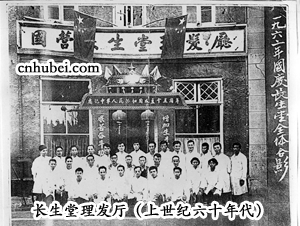 店员工上门服务。
店员工上门服务。
武汉理发厅:原名德记理发厅,位于中山大道江汉路旁(现佳丽广场处,已拆迁)。创立于1919年,素以理女性发式著称。有两层楼,一楼为男宾厅,二楼为女宾厅,曾设计出毛边式、长波式、云纹式等10种具有民族风貌和季节特点的发型,在许多老武汉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万国理发店:原址在现天津路八路军办事处内,解放后迁到汉口扬子街。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老店日本人特别喜爱光顾。尤以烫发著称。
此外,还有位于天津路巴公楼的上海美发厅,六渡桥香港理发厅,以及武昌司门口华安理发店、汉阳和平理发店,都是曾经响当当的老字号理发店。(非云)
………………
你眼中的武汉,是怎样的?
两江三桥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勾勒出她的雄壮和时尚,黄鹤白云和数十个城中湖的万顷碧波,展现着她如诗如画的柔情;商业传统、租界烟云、首义之城,历史的风云际会铭刻着她的名字;排档茶楼、小巷里弄、寻常人家,人间的烟火气又赋予了她亲切、随意和凡俗。
是的,她亲切、随意、凡俗,也不乏大气、明艳、庄重。她从不忌讳市井是她的招牌,红油爆起的人间烟火给她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她也从不拒绝外来文化的进驻,传统码头文化的包容让她如海纳百川般拥有了千万种的城市表情。
如果说“黄鹤楼中闻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青天无色月光微,新市场中火焰飞”描述了这里曾经的城市故事,那么今天,《城事周刊》封面将试图穿越时光隧道,将历史和现在对接,追忆属于我们的过去和描述属于我们的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