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是一份杂志,后来新文学史上却渐渐有了“现代派”的命名,且此“现代”就是指的《现代》杂志。一份开始宣称绝不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的期刊,后来却被追赠了一个某某派的谥号,是颇为滑稽的。我们说《现代》形成了一个“现代派”,大抵是因为两样东西,一是《现代》上的自由诗,一是《现代》上的新感觉派小说。
在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之后,占据着诗坛中心地位的,是“新月派”。“新月派”的来由,便是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新月》,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负责。说来有趣,被认为是“新月派”的人,譬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也是死不承认自己有“派”的,认为这只是左翼文人赠予的一顶大帽子。可是随着1931年9月陈梦家的一册《新月诗选》的出版,这个名称便渐渐坐实了。“新月派”在诗歌上的原则,便是格律。这一群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才子们,认为最好的诗,就是西方的十四行或者方块体,他们是讲究一种建筑美、音乐美与绘画美的。

可是《现代》并不如此,施蛰存曾专门列过一个名单,记载着在《现代》前三卷上发表过诗作的诗人和篇数,包括戴望舒、艾青、李金发、施蛰存等在内。这些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的诗歌不讲韵律,没有整齐的格式。譬如施蛰存自己在《现代》第1卷2期上的小诗《银鱼》:
横陈在菜市里的银鱼,
土耳其风的女浴场。
银鱼,堆成了柔白的床巾,
魅人的小眼睛从四面八方投过来。
银鱼,初恋的少女,
连心都要袒露出来了。
这样的诗与新月派音节整齐、形式完美的《死水》、《再别康桥》是很不相类的。一出现,就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有读者叫好并开始模仿,有读者却大喊看不懂,称之为“谜诗”,质疑这些诗歌“诗”的地位。对此,施蛰存做出了学理的回答,在第4卷1期,他发表了《又关于本刊的诗》,提到:
“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整齐,但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
”
施蛰存的解释,为自由诗争取了地位,因为他的位置所在,《现代》便成了当时自由诗的一个重镇。这些记载着诗人一个一个思想断片的诗歌不时在《现代》上出现,使《现代》形成了一股纯然不同于当时日常所见的新诗风潮。而施蛰存为《现代》的诗所做的解释,后来便成了现代诗的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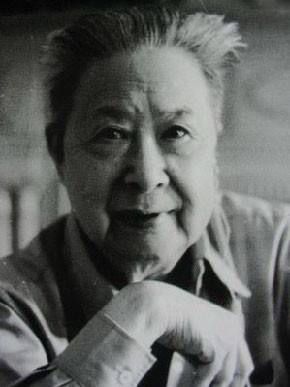
施蛰存
《现代》具有现代特征的另一个表现,是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小说。所谓新感觉派,是对1920年代川端康成、片冈铁兵等一批日本作家创作的指称。1924年,川端康成等创办了《文艺时代》,吸收多种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融入日本民族心理小说的创作特征,形成了注重感觉的一派小说。1928年,还叫刘灿波的文学青年刘呐鸥翻译了横光利一等人的小说集《色情文化》,算是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始。《现代》创刊号上,刊有穆时英的《公墓》,而他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也陆续在《现代》上出现。与穆时英近似的,有刘呐鸥。《现代》第2卷1期,同时刊登了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与刘呐鸥的《赤道下》。这两篇小说与同一期茅盾的《春蚕》以及下一期郁达夫的《迟桂花》不同,它们并没有多少故事,所描写的多是一片一片的感觉,表现着一种文学的新质,与《现代》上刊发的自由诗一样。

穆时英
施蛰存对二人十分欣赏,他说,“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贵的。”①施蛰存的眼光是开阔的,推荐也心怀诚恳,因为他自己也在写着心理分析式的小说,实验着白话小说的新式样。因了他们的创作,《现代》一度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但其实,在整个中国玩新感觉派的也没有几个人。我们现在认为的新感觉派代表刘呐鸥、穆时英,都是施蛰存的好朋友,有学者认为新感觉派的准备期是《璎珞》和《文学工场》,萌芽期是《无轨列车》与《新文艺》,成熟与衰落期是《现代》,那不过是把施蛰存早期的文学轨迹重述一遍罢了。

施蛰存曾说过办刊的好处,其一便是“对编者来说,是为了自己及朋友们发表文章的方便”②,在《现代》上,体现也是明显的。《现代》虽不是施蛰存创办的刊物,但近水楼台,他为自己的朋友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提供不少方便,谁想无意间竟造就了中国“新感觉派”的高峰,世上的事情有时真是难以预料。
施蛰存主编的《现代》透着一股股的现代气息,可谓渊源有自。施蛰存是上海松江人,他的生活也是洋派的③。这样的出身,使他对上海滩上的摩登气息有一种内在的认同。他欣赏这种洋场生活的新,并在《现代》上吸收它,发布它。沈从文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施蛰存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是沈从文的英俊之气消磨不少之后,“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④的结果。从《现代》上的自由诗与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大量翻译作品来看,施蛰存的立论不无道理。或许,浓郁的现代气息正是《现代》对于海派文学发展的意义,发展了海派文学的另一面。毕竟,与其同时而意气风发的“论语派”尽管不无外国血统,而呈现出来的却多是晚明士子的风气。
《现代》选择在上海文坛短暂的真空时期出现,一时成为文坛的中心。当时写稿的作家真可谓极一时之选,《春蚕》《迟桂花》《上海的狐步舞》《公墓》《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等,后来都成了新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但正如天宝年间繁华的瞬息落尽,《现代》的繁盛也十分短暂。在《创刊宣言》之中,施蛰存坦承,“这虽然是本志的创刊宣言,但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两字更为适当些”⑤,其原因,就是“当本志由别人继承了我而主编的时候,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

这份担心一年后就验证了。施蛰存独自主编的《现代》只有两卷,12期,1年的时间。从第3卷一起开始,就由施蛰存与杜衡共同署名主编,而这时“《现代》已不能保持每期一万册的销路”,其原因,“一则由于本身内容不免低落,二则生活书店的《文学》已异军突起”⑥。内容的低落,有杜衡的原因,“杜衡的参加编务,使有些作家不愿再为《现代》撰稿,连老朋友张天翼都不寄稿了”⑦;也有施蛰存的原因,如他和鲁迅的争论等,影响到了一些作家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施蛰存为《现代》预设的编辑主张开始慢慢变了味道。在这种情形下,再加上《文学》《论语》等其他刊物的崛起,《现代》便过了他的兴盛期,开始逐步滑落。从第4卷开始,每期就只有二三千册了,终究未能像“论语派”之于散文刊物一样,为综合文学期刊提供一个善始善终的运作模式。坚持到第6卷1期的时候,现代书局换了老板,施蛰存与杜衡辞职,《现代》又出了3期,便寿终正寝。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5年5月的6卷4期终刊,《现代》一共出版了34期,在海派文学的天际上划过了3年的痕迹。
参考文献:
①《社中日记》,《现代》第2卷1期,1932年11月。
②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北山散文集》第31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③ 施蛰存记述自己1928年暑假时的生活,“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参见《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北山散文集》第30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④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往事随想·施蛰存》第2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⑤施蛰存《创刊宣言》,《现代》第一卷1期,1932年5月。
⑥施蛰存《<现代>杂忆》,《北山散文集》第27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⑦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北山散文集》第3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作者简介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派文学》(合著)等,编选《出版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高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