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源是嘉道时期倡导社会变革的杰出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实行家。他既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又对实际的社会财政经济问题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清代的“漕、盐、河三大政”,“利弊之所薮,皆萃于江南”[1]。而魏源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于江南地区,又长期充当经世派地方大员陶澍、贺长龄的幕僚,在当时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而又百弊丛集的漕运、盐政和水利等部门中参与策划过颇有影响的改革,或者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以公羊学说为基础,融合《周易》《老子》《孙子》等中国传统变革思想的精华凝聚而成的变革理论,是魏源参与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重视“亲历”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推动他将变革的主张付诸现实中检验,将变革是必然规律、忧患意识等观念上的普遍认识,与提出具体的改革主张结合起来;思想家的身份,又使他具有将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升华为理论的高度自觉,从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思想成果,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着值得借鉴的方法论意义。

一、“勤访问”“亲历诸身”:注重调查研究
魏源认为,“人恒言‘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2]。他大力倡导知行统一的治学方法,主张到实践中去求取真正的学问,反对脱离社会实践的为学问而学问:
“及而后知,履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翻十四经之编,无所触发,闻师友一言而终身服膺者,今人益于古人也;耳聒义方之灌,若罔闻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亲于言教也。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啜。[3]
魏源从认识论的高度论证了知源于行、行先知后的道理,主张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判定认识的正确与否,体现出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正是基于进步的认识论观点,魏源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就是大量阅读前人文献,广泛进行社会调查,然后把亲身调查所得与书本知识加以对照,从而折中诸说,纠正前人错误,得出切合实际的见解。青年时代的魏源就曾有过“足不九州莅,宁免井蛙愚”[4]的意识。多年的治学经验更使他认识到“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众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的道理。因此,他提出,“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他提倡带着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不能“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5]。他早年求学京师,与政界学界人士往来酬酢,对官场腐败习气有深入了解,因而能够在人才问题上提出改革建议;中年担任江南督抚的幕僚,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问题,所以对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水利“诸大政”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改革方案。他曾实地考察过永定河、淮河、汉水、洞庭湖,写就《筹河篇》《湖广水利论》等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如《畿辅河渠议》一文写作之前,他曾于“道光甲辰、乙巳之春,两从固安渡永定河,详审南堤外如釜底,北堤外地与堤平,又质诸土人之习河事者”[6]。他曾游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半个南部中国,搜集资料,购买书籍地图,从而增补完成了《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为了写作《圣武记》,他不仅查阅了大量内阁档案文书,而且虚心向人求教,如当时的果勇侯杨芳曾“告以御炮之法”[7];关于清朝平定苗疆的事实,则出自参加这次军事活动的罗思举的口述。在协助陶澍、贺长龄试行漕粮海运的改革中,魏源对漕运积弊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长期从事漕粮运输、“身阅四朝漕”的太仓粮船水手陈阿三[8]。在写作《筹漕篇》之前,他曾经“霄旦讨论,寝食筹度,征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9]。大量的长期的细致的调查研究,使魏源掌握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他的改革主张援古证今,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能够从实际出发,其论证往往有针对性有说服力,提出的策略具有可操作性,在实行中取得了一定效果。

二、“兴利由于除弊”:坚持辩证观点
魏源从《周易》《老子》以及佛学等古代思想资源中吸取朴素辩证思想的精髓,对宋代理学家提出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10]这一命题进行了发挥。他指出,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对立面,同一事物内部也是“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 [11],甚至“一念之中,有屡舜而屡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12]。处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的对立双方,为什么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魏源分析指出,这是由于“有对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对立双方并非势均力敌,其中必然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且对立面是相互转化的。转化的动力是什么?他明确提出“反者道之动”[13],亦即对立双方的矛盾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转化,因为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中,斗争就不可避免:“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变,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这正是对立面转化的动力;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其结果是“偏胜者强[14];这个转化过程,是由微而著的渐进,寒冷只有发展到“极致”才产生“暑”,“动极必静,上极必下,曜极必晦”[15],而要打破对立面矛盾斗争的均势,实现转化,必须经过积聚力量的阶段。
以上观点,是魏源对于朴素辩证法的理论阐释。而在实践中,他堪称近代熟练而灵活运用辩证观点的思想家。从对立统一中把握矛盾,确立以“变”为核心的哲学观和历史观,使他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在分析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方面,往往发人所未发。利弊相倚的对立统一思想,使他得出了“兴利由于除弊,必知弊之所由,而后知利之所在”[16]的结论;从局部看全局的方法论,使他通过对治理黄河的历史考察而看到了全面改革的迫切性:“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17]他从两淮盐政改革中总结得出“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裕课必出于轻本,而绌课必由于重税”的改革规律,不仅适应于两淮,适合于盐政改革,而且对“漕赋关榷一切度支之政”都具有普适性[18];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两方面考虑,他提出“缓本急标”、“货先于食”的改革方案,既不触动“重本”的思想基础,又为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开辟了理论空间,具有很强的策略性。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魏源再次创造性地运用辨证思维的方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揭示出“师夷”与“制夷”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从而解决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学习西方与反抗侵略的复杂课题,成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思想指南。
三、“立乎今日以指往古”:涵养历史思维
魏源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建立在“公羊三世说”基础上的朴素进化历史观,使之能够正确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他反对“言必称三代”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完全割断“古”与“今”的联系:
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19]
在此,魏源将“治”与“学”分开来论述,是有深意的。在他看来,政治上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不能以古绳今;而学术上则以复古为要,不可以“执今律古”。魏源对政治与学术的这种经纬分明的划分,其出发点是一致的。道咸年间,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社会的变革迫切需要学理上的支持以及面向社会现实的学术风气的养成。然而,当时学术界的“今”,是盛行一时的汉学和官方提倡的理学,二者的治学路径虽然不同,但都脱离实际,无补于社会现实。于是,经过庄存与、刘逢禄的倡导而复兴的西汉今文经学,以其“以经议政”的传统、“三世说”的变易历史哲学和“微言大义”的论学特点,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的途径和合法的形式,为现实社会的变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舆论支持。魏源提出的学术复古路线,就是要求从“今”之汉学、宋学的空疏迂腐学风中走出来,借“古”之今文经学以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的治学传统,树立经世致用、立足社会现实的学风。他所标榜的学术“复古”,是打着复古的旗帜以“求解放”,其出发点仍然在于“今”,在于“治”。正如齐思和先生所指出的,“其学也,即所以为治也”[20]。而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拿历史的旧规来衡量当代,只能是矫诬和谬误,必须立足现实。因为时势在不断变化中,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环境和形势下、因不同的人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时代不同,所处的客观情势不同,人也不同:
同俭也,或以之养廉,或以之济贫;同礼也,或以之将孙,或以之济争;……故以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以迹师古,则不足以希古。[21]
在这里,魏源强调,如果不考虑当今实际情况,或盲目效法古制,或死守祖宗成法,不求变革,只能导致僵化和保守。不过,他并非全盘否定“古”,而是认识到古代政治的得失能为当今提供借鉴,并提出处理古今关系的正确方法是“今必本夫古”,古又“必有验于今”[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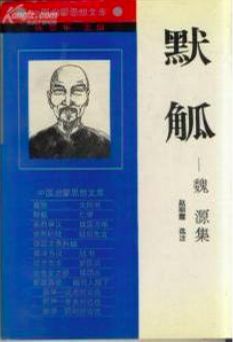
基于对古今关系的辩证分析,魏源明确提出以“便民”作为评价政治好坏和进步与否的标准。他认为,往往是对陈腐的旧例改革得越彻底,就越能给老百姓带来更大利益:
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屯田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彍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23]
魏源认识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旨归,总结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历史规律,为变法主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通过分析历史为现实提供资鉴,是魏源论学论政的重要方法。他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无一不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认识:一是从历史事实中发现问题。如仿铸西洋银钱和开采银矿的主张,是他认真分析洋银流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历代货币币材的变化,了解到中国的银矿尚未全面开采等情况后而提出的;二是从古今对比中说明问题。他从海上航线的变化、运输船支的性能、运输人员的技术水平等方面比较了元代与道光时期的变化异同[24],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海运在当前形势下的可行性;他在《筹河篇》中提出的“令河北决”、“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的宏论,堪称对中国宋元以来治河经验的全面总结。
正是因为有了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的思维方法和立足现实以观往古的历史观,当鸦片战争的巨变骤然而来的时候,魏源才能够引领时代风气,自觉运用中西比较的思维方法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新问题,进而将改革的方向从“古时丹”转移到“夷之长技”。他编撰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把中国与西方、与世界联系起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西差距,思考救亡图存之道,传达了初步的世界意识和世界眼光。
参考文献:
[1][2][3][4][5][6][8][9][11][12][14][16][17][18][19][21][22][23][24]《魏源集》,第244、35—36、7、576、35-36、 382、836、418、18、2、239、442、373、440、48、46、156、47-49、418-419页。
[7]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卷五,第92页。
[10]《明道先生语一》,《二程氏遗书》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4页。
[13][15]魏源:《论老子三》,《老子本义》页三、页一。
[20]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2月第39期。
作者简介

刘兰肖,历史学博士。编审。主要从事新闻史、出版史、出版学、出版文化、新闻出版宏观管理等方面研究。已出版《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魏源评传》(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期刊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专著,发表专业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