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抄纂,就是“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1]。它的特点是对原文进行原封不动的辑录,新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原作整体性的内容,像先秦子书《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杂家言》《百家》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除了子书的抄纂外,将其他单行的诗文篇目汇编成集,也属抄纂的范畴,因为它也是原封不动地辑录原文。而实际上,古代抄纂的对象不限于子部和集部,几乎任何类型的文献都可以成为抄纂的对象。对于抄纂而来的内容,还要以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予以编排,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文献体裁,如类书、杂钞、总集、别集、丛书等。
类书是古代抄纂的重要文献类型。所谓类书,就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利寻检引用的一种工具书。因其内容包罗万象,又有古代百科全书之称。我国古代类书数量众多,据台湾学者庄芳荣所编《中国类书总目初稿》(台湾学生书局1984版)参考历代史志、公私藏书目录及15家今人目录,计得历代公私类书824种,扣除同书异名和疑为同名书者,计766种,远超前人的统计数目。类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采获群书,以类相从,即将原文整段、整篇乃至于整部书抄入,而不加篡改,然后按既定的类例重新编排。这当然会涉及图书的著作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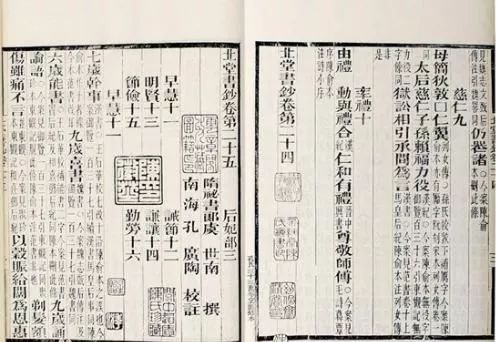
类书起源于曹魏时期的《皇览》。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及军阀混战,造成了图书的严重散失。魏文帝曹丕爱好文学著述,深知文化典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在他执政的七年中,采取了采拾亡遗、搜集图书的措施。据《三国志》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2]该书编成于魏皇初元年(220),凡八百余万言,参与其事的有王象、缪袭、桓范、刘劭、韦诞等人。清孙冯翼《问经堂丛书》辑本《皇览》序言:“其书采集经传,以类相从,实为类书之权舆。”《皇览》虽已亡佚,但引用该书条目的其他古书仍有部分存在,如《太平御览》引《皇览·冢墓记》20条,并多次引《皇览逸礼》;《水经注》引《皇览》13条。其他如《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史记集解》等,也都引用过《皇览》的条目。把这些条目集中起来,亦可窥见《皇览》的部分内容。该书为迎合帝王的需要,内容主要偏重前朝掌故、文人轶事、名臣言行、宫闱趣闻、帝王之术及典章制度等方面,不像后世的类书那样内容无所不包。《皇览》的编纂手法主要是割裂古书,寻章摘句,以类相从,即将经传中的文字材料按一定的需要辑录出来,分门别类地编排,以便皇帝阅览。
自《皇览》开创类书摘抄旧书,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后,后世纷纷仿效。晋代类书有陆机《要览》、虞喜《志林》、韦谀《典林》等。南北朝崇尚骈偶排丽,讲究用典使事,写文章可以博采纪传旧事和前人诗文旧辞。因此,王公贵族竞相聚集文士,大兴类书编纂之事,如南齐东观学士奉敕编纂《史林》、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集学士编纂《四部书略》、南梁徐勉奉敕编纂《华林遍略》、梁简文帝萧纲敕陆罩纂《法宝联璧》。可见,帝王贵族往往是类书编纂的直接推动者。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类书的编纂可使贵族成员尽快熟悉和掌握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另一方面也可宣示王朝的文治之功。这一时期编编纂的类书还有南梁刘峻《类苑》、刘杳《寿光书苑》、陶弘景《学苑》、张缵《鸿宝》、朱澹远《语对》《语丽》;南陈张式《书图渊海》;北魏崔安《帝王集要》、元晖《科录》;北齐祖珽《修文殿御览》等。另外还出现了不少宗教类专科类书,佛教类的如刘宋沙门昙宗《数林》、释僧璩《僧尼要事》;南齐比丘释王宗《佛所制名数经》、释超度《律例》、萧子良《僧制》《三宝记》;南梁释宝唱《经律异相》、释法超《出要律仪》、释僧祐《世界记》、释僧旻《众经要钞》、释智藏《义林》、虞孝敬《内典博要》;北齐释法上《增一法数》;北周释静蔼《三宝集》等。道教类书也已出现,如北周时期的《无上秘要》等。这部书原100卷292品,是在周武帝灭佛的历史背景下,由通道观道士帮助宇文邕完成编纂的。
隋朝享国虽短,却也编了不少类书,举其要者,有柳䛒、虞绰、虞世南等编纂的《长洲玉镜》,杜公瞻奉敕编纂的《编珠》,诸葛颖辑的《玄门宝海》。唐代类书编纂之风日盛,官修、私修类书相得益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体例严密,品类丰富,选辑精当。官修类书有高祖时欧阳询领衔纂修的《艺文类聚》,太宗时高士廉等纂修的《文思博要》,高宗时许敬宗等纂修的《瑶山玉彩》《累璧》,武后时有题名为天后撰的《玄览》(实由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等编纂)、张昌宗等纂修的《三教珠英》,玄宗时徐坚等纂修的《初学记》等。私修类书著名的有虞世南《北堂书钞》、陆赞《备举文言》、元稹《元氏类集》、白居易《白氏经史事类》(又名《白氏六帖》)、温庭筠《学海》、李商隐《金钥》、皮日休《皮氏鹿门家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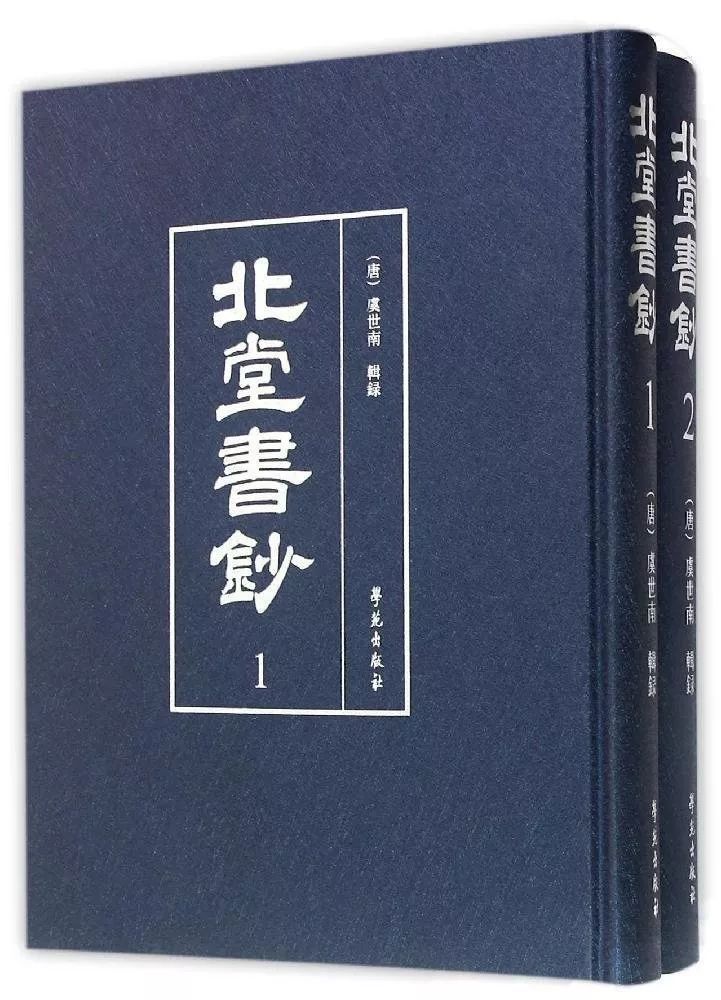
隋唐类书在采摭资料时时,注意标引出处。据孔广陶统计,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北堂书钞》所引图书,除集部外约800多种。它每种书采获引文多至一千数百条,少则三两条。其引书的年代断限,“皆三代、汉、魏,迄于宋、齐。最晚者沈约《宋书》、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后魏书》;其诗、赋、颂则颜、谢、鲍为最晚;陈、隋只字不钞。”[3]其编纂体例是在每一类目下,把典籍中有关的材料汇集在一起,每一事摘出一句,然后以小注的形式说明文句的出处、上下文以及有关的解释,注文中间或出现虞世南的案语。如卷九五“艺文部经典一”“六籍”之下有:“班固《东都赋》云: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谨案:六籍,六经也。”再如,《艺文类聚》卷八一“药香草部上·菖蒲”子目下征引了10种相关文献资料,这些引用的文献资料,均注明出处,标示书名、篇目、作者和文体类别。《艺文类聚》以后的类书,大多沿用这种形式,只是罗列文献资料的形式略异。类书注明所抄原文的出处,除了方便核对引文和提高可信度外,也是表明对原作的一种尊重态度。
入宋以后,类书的编纂迎来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官方编有著名的四大类书,即《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民间私修类书著名的有吴淑《事类赋注》、高承《事物纪原》、潘自牧《记纂渊海》和王应麟《玉海》等。太平兴国二年(977),李昉等受诏编纂《太平御览》,至八年(983)书成,计1000卷。该书类分55门,门下又分4558个子目,征引至为浩博。据洪迈《容斋随笔》称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书1690种,如果加上所引诗赋,则达2800多种,如天部“太始”条顺次征引了《易·乾凿度》《帝王世纪》《楚辞·天问》(包括王逸注)、张衡《玄图》和阮籍《大人先生传》。这些资料,既注明了出处,又大多是原文照录,为读者提供了便利。《太平御览》之前的类书引书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正文、注文连写而不加区别,如唐代的《初学记》《艺文类聚》都征引了北周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它们在处理正文和注文时就未加区分。而《太平御览》却克服了这一毛病,将正文和注文区分得十分清楚。这说明编者在编书时不是简单地采录前代类书,而是检核了不少引文的原文。
但《太平御览》在引书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所引书名不尽统一。如刘澄《宋永初山川古今记》就有《宋永初山川记》《永初山川记》《山川古今记》和《刘澄山川记》五个异名。其次,书名与篇名相混淆。如《〈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即引书目录)所列《立后土国语》《讽谏木国语》《见君大韩子》《杀谏庚符子》,不像书名而更像篇名,不当与书名并列。再者,有些引文脱略书名。如卷二七一引刘向《新序》论兵事,其“又曰”云:“乐毅以弱燕破强齐七十余城者,齐无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绍五万者,袁无法故也……。”[4]这里所谓“又曰”,按其通例,是继续征引刘向《新序》。然而西汉刘向怎么可能叙述东汉末年曹操、袁绍间的战事呢?显然有违常理,“又曰”前当脱略了另一书名。
《册府元龟》1000卷,由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纂,自真宗景德二年(1005)始,至祥符六年(1013)成。该书分31部,其下又分1104门,“其书止采六经、诸史、《国语》《国策》《管》《安》《孟》《晏》《淮南》《吕览》《韩诗外传》,及《修文御览》《艺文类聚》《初学》等书。即如《两京杂记》《明皇杂录》等,皆摈不采。其编修官供帐饮馔,皆异常等。王钦若以《魏书》《宋书》有‘索虏’‘岛夷’之号,欲改去。王文正公谓旧文不可改。又如杜预以长历推甲子多误,皆以误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诏,凡悖逆之事,不足为训者,删去之。复亲览,摘其舛误,多出手书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5]但《册府元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引文不注出处,如:“汉文帝即位十七年,改元后元年。(注云):‘新垣平候日再晕,以为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尽七年。”再如“(武帝)元鼎元年。(注云):‘得宝鼎,故因是改元。’尽六年。”[6]前引注文乃《汉书》张晏注,后引注文乃应劭注,《册府元龟》皆不予注明,这是对前人作品的不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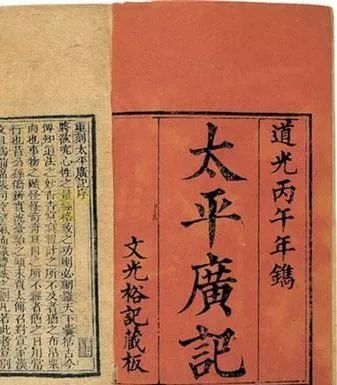
《太平广记》500卷,亦由李昉奉敕监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王克贞、张洎、董淳、赵邻畿、陈鄂、吕文仲、吴淑等12人。该书按题材分92类,下分150余细目,每一细目下再列事目,每条事目都征引原文,并注明出处。如“神仙”诸条,分别引自《神仙传》《神仙传拾遗》和《洞宾记》三书。《太平广记》前列引用书目共343种,其中《妖乱志》《河洛记》复出,实为341种。然书中所引远不止此数,其中不见于卷前引用数目者138种,实引书凡479种。
金、元因历时不长,所编类书很少,如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完颜纲等奉敕编有《编类陈言文字》,今已失传。元文宗时期,赵世延、虞集等奉敕编《经世大典》。元代私修类书有胡炳文《纯正蒙求》、严毅《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高耻传《群书钩玄》等。
明代类书数量较多,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150部左右,著名的有《永乐大典》、俞安期《唐类函》、顾起元《说略》、章潢《图书编》、邹道元《汇书详注》、唐顺之《荆州稗编》、徐元太《喻林》、王志庆《古俪府》、彭大翼《山堂肆考》、焦竑《类林》、王圻《三才图会》等。
明代类书与前代相比,质量普遍下降了不少。如唐顺之《荆州稗编》虽然订正了不少所引书名、人名,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程大昌《诗议》在所撰《考古编》中,而乃以为出自《新安文献志》;《正谏》本《说苑》篇名,而标之为论;《林泉高致集》所载荆浩《山水赋》、李成《山水诀》乃其人所自作,而概以为出郭思之手;敖陶孙字器之,而讹作孙器之。”[7]董斯张《广博物志》,“其征引诸书,皆标列原名,缀于每条之末,体例较善。而中间亦有舛驳者,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采摭古书,原名具在,乃斯张所引,凡出自二书者,往往但题《御览》《广记》之名,而没所由来,殊为不明根据。又图经不言某州,地志不言某代,随意剽掇,亦颇近于稗贩。”[8]以上所举,有的显然扰乱了古代著作权关系。徐元太《喻林》,自序称引书400百余种,而检其所列书名,实不逾半,有夸大之嫌。该书引书用程大昌《演繁露》之例,皆于条下注明出处,亦迥异于明人剽窃扯挦之习,但错误却不少,“如‘儿说宋人善辩者’一条,本出《韩非子》;‘周人有仕不遇者’一条,本出王充《论衡》,皆引《艺文类聚》;‘怀金玉者至不生归’一条,本出《后汉书·耿弇传》,而引《文选》李善注;‘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一条,本出刘知几《史通》,而引《事文类聚》;‘天寒即飞鸟走兽尚知相依’一条,本出沈约所作《阮籍咏怀诗》注,而亦以为李善。此类颇多。又如以杜预、何休、范宁为汉人,以陈寿为魏人,以李善为隋人,皆时代舛迕。申培《诗说》《天禄阁外史》《武侯心书》之类,皆明代伪书,不能辨别。《广成子》本苏轼从《庄子》摘出,偶题此名,乃别为一书。无能子,云不知何代人,皆未免失于疏略。”[9]
明代类书也有质量相对较高的,如王志庆《古俪府》,仿欧阳询《艺文类聚》之例,“或载全篇,或节存本,与他类书割裂饾饤,仅存字句者不同。所引止于宋以前。又皆从各总集、别集采出,亦不似明人类书辗转稗贩,冗琐舛讹。惟间收《玉海》所载偶句,稍为猥杂。”[10]明代类书大抵剽窃饾饤,无资实用,而顾起元所编《说略》比较注意引书来历,“尚颇有体裁。凡所采摭,大抵多出自本书,不由贩鬻,其史别、典述诸门,尤为有益于考证。”[11]明人类书大都隐其出处,以至于凭臆增损,无可征信,但陈耀文所编《天中记》虽援引繁富,却能一一著所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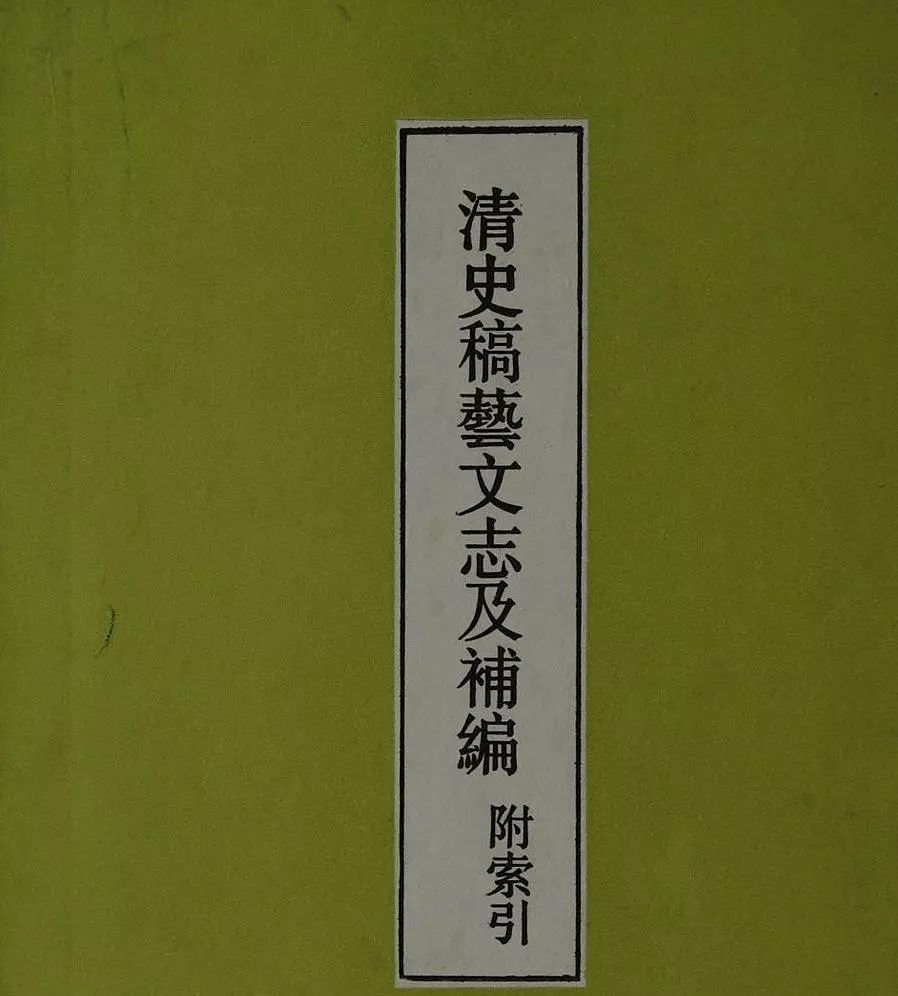
清代类书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共计146部13847卷。其中较著名的有陈梦雷等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张玉书等编的《佩文韵府》,张廷玉等编的《子史精华》,陈元龙等编的《格致镜原》等。清代几部高质量的官编类书,都能尊重原作者及其作品,如《佩文韵府》就比较注意标明引文出处,“其一语而诸书互见者,则先引最初之书,而其余以次注于下。又别以事对摘句附于其末。”[12]《格致镜原》针对明代类书引文不载原书之名的陋习,对之加以考订,所出必系以原书之名。
倒是一些清代民间私修的类书,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朱昆田编《三体摭韵》,采集前人新艳字句排纂而成,但其引文却存在不少问题,“即以一东韵而论,阿童为王濬小字,见《三国志注》,乃云出苏轼诗;鹤氃氋而不舞,乃羊祜事,见《世说新语》,乃云本陆龟蒙诗。此犹云惟引词赋,不及子、史也。至于椒风殿名见《两都赋》,乃引崔国辅诗。唐弓字见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乃引贺知章诗。比红儿自有罗虬本诗,乃引陆游诗。”[13]宫梦仁编《读书纪数略》54卷,大抵以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张九韶《群书拾唾》为蓝本,而稍摭宋、元、明事附益之。该书引书出处,凡例虽称“题下必注某书,示不忘本也”,但并没有完全做到,“其间多有不注者,大约世所习见之书,亦或钞时偶忘”[14]。其他如王文清编《考古原始》6卷,不著出典,益不足征。汪文柏编《杜韩集韵》3卷,所摘之句,不著原题。杨拥编《是庵日记》14卷,采辑群书,分类排纂,但“各注所引之书名,亦间附以己意。其凡例自云:‘会心即录,叙次不伦,挂漏孔多,体殊握要。’盖亦随意撮抄之书也。”[15]朱虚编《古今疏》15卷,征引浩繁,但不详所出,旧文与新义相杂乱,这些都是历代抄撮成书的通病。
注释
[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7.
[2](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88.
[3](清)严可均.铁桥漫稿·卷8.清光绪十一年(1885)长洲蒋氏心矩斋刻本.
[4]转引自: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述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6.
[5](宋)袁褧.枫窗小牍·卷下.中华书局,1985:29.
[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5·帝王部·年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荆川稗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1790.
[8](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广博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1794.
[9](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喻林.北京:中华书局,1997:1791.
[10](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古俪府.北京:中华书局,1997:1794.
[11](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说略.北京:中华书局,1997:1792.
[12](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佩文韵府.北京:中华书局,1997:1796.
[13](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9·三体摭韵.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1.
[14](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读书纪数略.北京:中华书局,1997:1797.
[15](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9·是庵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3.
【作者简介】

李明杰,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文献学和中国图书文化史。近十余年来,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项;著有《宋代版本学研究》《中国出版史(古代卷)》《中国古籍版本文化拾微》《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等,发表论文7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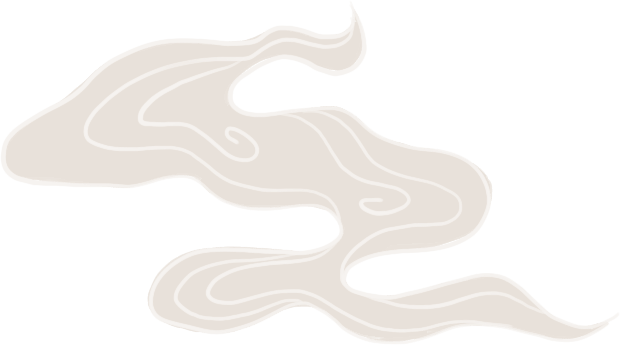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