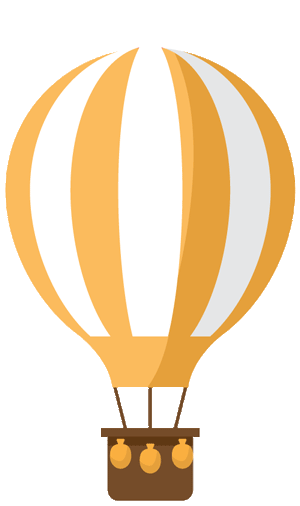《废名诗集》即将出版了,这是诗坛上一朵迟开的花,同时也将是迟谢的。“废名是诗人”,渐渐已成公论,然而长久以来读者并不能读全他的诗。此次《废名诗集》出版,将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废名1949年以前的诗106首全部收入,包括两首旧体诗和两首译诗。另外,“为便于读者了解、理解废名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特选《新诗问答》、《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妆台〉及其他》等7篇文章列为附录”(陈建军:《〈废名诗集〉前言》)。至此,诗人废名浮出水面。

废名
废名的诗以前大体辑印过三次。一是1944年新民印书馆出版的《水边》,主要是废名的作品,所以一般认为该集的作者是废名。解放前乃至今天不少读者都是通过它集中领略诗人废名的诗才的。二是1985年出版的冯健男编选的《冯文炳选集》,共收废名解放前的诗27首。新时期以来的读者大多以此为蓝本欣赏和研究废名的诗歌。三是1993年周良沛编的《新诗库三集.废名卷》,将废名生前公开发表的诗以及冯健男提供的三首未刊手稿全部收入,因此也为编者所认为废名的诗已经全部汇集于此。这样废名跻身百名诗人之列,似乎已锁进新诗库,没有更多的可能。不久随着废名佚诗的不断发现,才知道废名的诗有200首以上,“废名的诗大约仅存30首”的说法也由此打破。可惜废名的《天马诗集》已大多散佚,因此此次出版的《废名诗集》大约只占废名全部新诗的一半。
诗人废名的诗歌创作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早期诗歌截至1926年止,浅显易懂,大多发表在民国最早的新诗刊物《诗》上(叶圣陶、朱自清等编辑)。1922年废名以发表新诗登上文坛,此时的诗歌有的反映初到北京的农村求学青年欲冲破礼教束缚而又胆怯的心理,有的则反映五四退潮后一代文学青年的焦灼、苦闷,同时废名的视角也触及到下层人民生活,这些诗往往是思想和感情的碎片,闪亮、深切。如“白天里我对着一张纸做我的梦/夜间睡在床上听人家打鼾/讨厌的人们呵/你们就在梦里也在打搅我”。这些诗歌较为一般读者易于接识的是《冬夜》和《夏晚》,风格朴实清新。废名的早期诗歌放到新诗史上看待则体现了新诗草创之初的幼稚、直露。
进入三十年代后,新诗开始趋于成熟、繁荣。废名这一时期的诗歌诗风古朴、晦涩,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风格,也体现废名在实践自己的新诗观上所做的努力。《废名诗集》中共收录八十首,代表诗人废名的主体风格和最高成就。总体说来,大致有三大特点:
一是散文化倾向。废名的诗往往是兴笔所致,挥洒自如,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同时废名又是运用经济的文字,废名说:“我过去写的新诗,比起随地吐痰来,是惜墨如金哩!”(废名:《谈谈新诗》)废名将古文言字词运用到新诗的语句当中并活用典故,即是极大的尝试和探索。如“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将吴梅村的诗句直接引入,嫁接得多么自然,毫不费力气。
二是以禅写诗。1922年废名怀着一颗极大的向往之心来到北京,不久却是面临新文学阵营分裂、论争之时,于是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随后1927年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北平文人纷纷南下,北方文坛显得格外冷清寂寞,废名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心理由苦闷趋于封闭,性格更内向,思维方式侧重于内省,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废名找不到可辩清方向的思想作指导,于是躲进西山参禅悟道。汪曾祺、卞之琳都曾以此时的废名为原型刻画一个“深山隐者”形象。此时废名思想艺术的变化很明显表现在他的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上,以至他的朋友温源宁教授怀疑他受英国的伍尔芙、艾略特影响,然而不单是小说,这一变化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上。至此废名诗风大变,内容颇费读者猜详。废名以禅写诗,读者应该以禅读诗。苏轼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废名的许多诗句看似半通不通,无逻辑可言,其实他的诗像李诗温词一样,表面不能完全文从字顺,但骨子里的境界却是高华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鳃雪”谁又能只通过字面而不借助想象和领悟去理解呢?废名大约是最早将禅引入新诗的诗人,1947年黄伯思在《关于废名》中指出:“我感兴趣的还是废名在中国新诗上的功绩,他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中国新诗近于禅的一路。”废名的这些诗大多成于一时,“来得非常之容易”,有的是吟成的游戏之作,不可与之较真,亦不可轻易放过,因为里面“实在有深厚的力量引得它来,其力量可以说是雷声而渊默”。如“我倚着白昼思索夜/我想画一幅画/此画久未着笔/于是蜜蜂儿嘤嘤地催人入睡了/芍药栏上不关人的梦/闲花自在叶/深红间浅红”。废名的诗像晚唐诗词一样有“担当(寂寞)的精神”和“超脱美丽”(废名:《关于自己的一章》)。
三是美与涩的交织。废名的诗美是天然的,诗情是古典的,往往令读者有一种丈二和尚摸不找头脑的美丽,有仿佛得之的感觉。这是废名的诗晦涩的表现。废名的诗融儒释道为一体,并有现代主义之风,使得废名的诗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废名就曾以《掐花》为例说它是“新诗容纳得下几样文化的例证”(废名:《〈小园集〉序》)。废名有的诗确实难懂,如“黄昏街头的杨柳/是空中的镜子/对面小铺子的电灯/是寂寞的尘封/晚风将要向我说一句话/是说远天的星么”。真是诗人将要呓语,是说一首诗么?
抗日胜利后,废名再一次经历思想大变,这一时期尽管只有四首小诗,却不可小觑。废名经历九年跑反、避难,开始同情于“人类的灾难”,痛恨于“人类的残忍”,呼吁和平,诅咒战争,追求真理。
读废名的诗不可不读他的《谈新诗》。二者互为参照,也许诗就好懂多了。这方面的典范是沈启无为废名出版的《招隐集》,既有《水边》中的诗,又有《谈新诗》中的部分重要章节。不管怎么说废名的诗难懂又是公认的,刘半农、朱光潜、沈从文、艾青、吴小如等都这样认为,诗人废名恐怕很难觅得知音。但我们应该知道,废名说:“我偶尔而作诗,何曾立意到什么诗坛上去”(废名:《〈天马〉诗集》),而沈启无作诗则是废名鼓励的结果,两人都无意为诗人,却能有“共赏之趣”,他们作诗都只是私下爱好而已,并且沈启无有感激废名的意思。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沈启无出于怀念废名出版废名的诗集并作诗序《怀废名》,还将自己的诗作为附庸列于书末,明显有怀念他们一起“共赏之趣”的日子,而沈启无后来又出版《招隐集》自是深深懂得废名诗的缘故。这样看来,沈启无算得诗人废名的一个活知音。关于沈启无出版《水边》、《招隐集》,编者陈建军先生(另一编者为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在“《废名诗集》前言”中有公正评判。
近几年来,废名诗人之名日盛,这对于小说家的废名不知是否幸事,而《废名文集》出版后,有人说废名散文成就最高,不知《废名诗集》出版后是否有论者说废名诗歌成就最高!其实,作为小说家的废名和作为诗人的废名取得最大成就几乎成于一时,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只不过当时人们只看到小说家废名罢了。废名的诗具有前卫意识和探索色彩,以戴望舒、卞之琳和废名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上承诗体解放,自行摸索新诗出路并身体力行地批评二十年代新月派反动诗潮,下启八十年代诗歌的繁荣局面,废名也为新诗的成熟立下开拓之功。
作于 2004年9月
作者简介

眉 睫 原名梅杰,1984年生,湖北黄梅人。研究现代文学、儿童文学。曾任海豚出版社策划总监、社委会委员,现任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首席编辑。主持出版《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英、韩等文版)、《丰子恺全集》,主编《林海音儿童文学全集》等数百种儿童文学读物,并参加《荆楚文库》中《邓文滨集》《喻血轮集》《喻文鏊集》的点校工作。2014年荣获“中国好编辑”称号。著有《朗山笔记》《关于废名》《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童书识小录》《丰子恺札记——泛儿童文学随札》《黄梅文脉》《梅光迪年谱初稿》。编有《许君远文存》《梅光迪文存》《绮情楼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