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有一群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年轻人,他们用质朴的笔吼出了失去故土后的痛楚以及抗争的决心。这批后来被称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青年人,除了上次说的萧红,还有她的朋友萧军、骆宾基与罗烽等人。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今凌海市)一个贫苦家庭。早年的萧军曾在军队中担任书记员,“九·一八”事变后,因组织抗日活动失败,潜逃至哈尔滨卖文为生。1932年,萧军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接近了陷入人生绝境的萧红,英雄救美般地帮助她脱离了苦海。此后,两人相濡以沫,开始了困苦的文学生涯。1933年,萧军萧红分别署名三郎和悄吟,在哈尔滨自费出版了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成为这段生活的一个印迹。1934年6月,为了躲避日伪的追捕,萧军流落青岛,并在这里第一次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信。对于这个笔名,萧军后来曾解释它的含义:“萧是我喜欢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又因我家是东北辽宁义县,这地方曾为辽国京城,辽为萧姓。军是我的出身”。

萧军与萧红
1934年11月初,萧军与萧红来到上海,得到了鲁迅的关爱。对这两个年轻人,鲁迅不但借款资助,而且还设饭局为他们引见茅盾、聂绀弩等人,帮助他们进入上海文坛。1935年7月,在鲁迅的推动之下,萧军出版了长篇处女作《八月的乡村》。鲁迅专门写序,并不吝赞美:“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通过鲁迅的延誉,萧军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进入了创作上的黄金时段。三年的时间里,在《八月的乡村》之外,出版了中篇小说《涓涓》、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等五个集子,并于1936年春开始了鸿篇巨制《第三代》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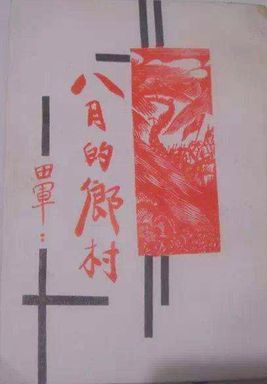
萧军的成功影响了骆宾基。骆宾基(1917—1994),原名张璞君,生于中俄朝边境的吉林省珲春市。1936年,正在哈尔滨筹办文艺刊物的骆宾基,听到了《八月的乡村》在上海出版的消息,而且还听说鲁迅专门给写了序,让骆宾基颇为羡慕,决定如法炮制。当年五月,骆宾基来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一出手就是一部长篇《边陲线上》。写了一半的时候,骆宾基给鲁迅写信,希望得到指点。可惜此时的鲁迅已经病卧,无法给骆宾基看稿子了,只能回信婉拒。不久之后鲁迅病逝,让骆宾基感到既悲哀又失望。稿子全部完成之后,骆宾基把稿子转给了茅盾。像鲁迅对待二萧那样,茅盾对骆宾基的处女作也热心推介。虽然先后被生活书店和良友书店两次退稿,但茅盾依然为之奔走,最终在1939年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边陲线上》还在寻找买家期间,抗战开始了。骆宾基顾不得书稿的命运,投身于上海的一些救亡活动,并以此为背景,写了《大上海的一日》等报告文学篇什,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刊物《呐喊》(后改为《烽火》)之上。对这些文字,晚年的骆宾基认为这是他走上文坛的真正起点。1937年11月,随着战事失利,骆宾基转赴浙东,此后几年间,辗转于皖南、桂林、重庆等地。其中1940年到1944年在桂林的时候,骆宾基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写出了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长篇小说《姜不畏家史》第一部等现代文学名篇。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骆宾基第二次来到上海。这次只待了半年时间,1947年2月初离沪赴京。在此期间,骆宾基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由于爱》、《可疑的人》两篇小说,并在《文萃》上连载了《萧红小传》。

左为骆宾基年轻时,右为《黄金时代》中黄轩的扮相
在东北作家群里,与骆宾基一样想见鲁迅而未得的,还有罗烽。罗烽(1909—1991),原名傅乃奇,辽宁沈阳人。1929年,罗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两小无猜的表妹白朗结婚,成为东北作家群中二萧之外的另一对伉俪。1935年7月,刚刚出狱的罗烽夫妇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同年11月,罗烽夫妇通过周扬加入了“左联”,开始进入现代文坛的主要舞台。到上海之后,罗烽写信给鲁迅,希望一见。鲁迅答复说天热,又忙,以后再见吧。孰料一等就是永诀,直到鲁迅去世,这次会面也未能实现。罗烽在上海的时间也不长,“八·一三“之后不久,罗烽就经南京去了武汉、重庆等地,并在1941年到达延安。在上海的两年间,罗烽与舒群等一起创办了刊物《报告》,发表了中篇小说《归来》。并于1937年由赵景深主持的北新书局出版了包括《第七个坑》等名篇在内的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

萧军、骆宾基和罗烽的创作,代表了“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粗犷热烈一脉。无论是作品内容的选材,还是写作的语言笔触,他们的作品都显得线条刚硬。这与三个人的身份有关。他们都既是作家,也是革命者。离开上海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或在解放区,或在国统区,都从事着革命工作,骆宾基还为此入狱两次。对他们来说,革命就是文学,文学就是革命,是一种一体化的存在。所以他们的作品相较于萧红和端木蕻良等人来说,显得更为雄壮,更为粗砺。

《黄金时代》中的罗烽白朗夫妇
自然,这也与他们的性情有关。1939年在成都时,萧军给罗烽夫妇送了礼物——两把锋利无比的小尖刀,意思是既可以自卫,又方便自杀,算是“老朋友的一点情义”。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慷慨之气。这种大爱,在面对底层人民的凄惨遭遇时,有时又幻化成一种同情和哀婉。就像硬币的另一面,在作品中,用细腻的柔情丰富着赤子之心的含义。
作者简介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派文学》(合著)等,编选《出版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高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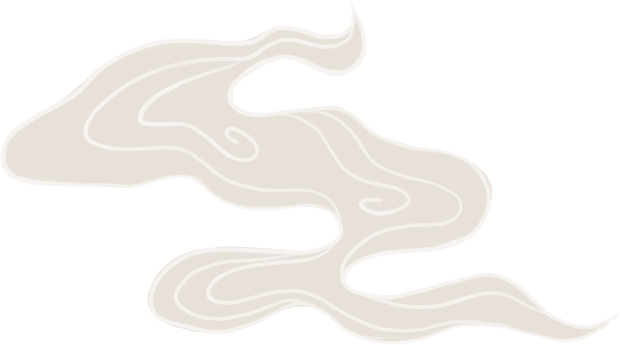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