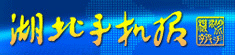���ѹʽ����ҳ������������ӿ���ĥ�����߹���������
����
�����ҷdz����ҵĸ��ס�������ƽ�Ļ��䣬������һ�־�ľ������ܡ�������������һ��ƽ�����ˣ�������ƽ�����̺���Խ�ķܶ���������һ�����Ծ�ǿ���ˡ�����Ŀ����Զ�����Ž�������죬�������������Ժ����м������ĵij��Ŀ�꣬�дﵽĿ�����ʵ�ƻ���������ֱǰ������ҡ�ļᶨ��־����һ��ʱ���ڣ�ͷ����ֻ��һ��ѹ��һ�еĴ��£�Ϊ������£�����ϧ��������ϧʱ�䣬ȫ���Ը�����Ҫʱ���������������������������ţ��������106���ˡ�
����1899�꣬�������ں���ʡ��ɽ��Ⱥ��֮���һ��С�������Ϊ��ƶ���˾���ʱ���ò��ѧ��ţ�������и����ᵽ������顣1915�궬�����������"������Ժ"�������߶��飬����1928�����200�����������Ե�һ����¼ȡΪ����ʡ�ٷ���������
���������������ױ��Ǵ�ѧѧϰ������������ѧλ��ѧʿ��˶ʿ����ʿ�������ĵ�ʦ���������������Ҷ�����Ϊ"���ǵ�һѧ��"��������ע�رȽϽ�����̽�֣���DZ���ڽ�������֮�о�����������ؾ��쵽�����ֲ����ӽ�������ʱ�ڵ��й����������Ѽ����ȱ�����ǽ�����ҵ�����һ����Ҫԭ�����IJ�ʿ�����ԡ��й���������֮�Ľ���Ϊ�⣬�ܵ��й����������������������ĸ߶������Ϊ֮��������д�������Ĺ���"�ڽ���ѧ�뾭��ѧ֮��Ե��������˿����Ե��о���������"��
��������д��ʿ�����ڼ䣬����δ�����Ѿ���ʮ���꣬���ܾõȣ�������˽���ˡ�Ϊ��һ����д�����ģ����Լ�ǿ��������ʧ����ʹ����һ�ߣ�ȫ���Ը���ѧ�ʡ���ò�ʿѧλ����������������������ͻ��ýϸߵ�����λ����Խ�Ĺ������������������һ����ԣ��ʵ�ļ�ͥ������������Щ���ܶ�ҡ���ع��ľ��ġ�������ǧ����࣬ѧ�����ɣ�����Ϊ���Լ�ƶ�����������������ǿ�ҵij���֮�飬Ҫ���Լ���ѧʶΪ���������־Ϊ��չ����Ľ�����ҵ�ܶ�������
����1935�길�ع���Ԫ�����������ټ��������������"���ٺ��������ᣬ�ɶ�����������"��ʾ���������Ⱥ����Ϻ����Ĵ�ѧ������ѧϵ��ϵ���Σ������Ŵ�ѧ�����݄��ڴ�ѧ�ν̣��ڹ��ݻ�ˮ��ԭ������������ѧԺ��ʵ��������Σ���ѧԺΪ�廪��Э�͡��Ͽ����ྩ���������ѧ�ϰ죻�������������ϵ�Լ�������ѧ����ϵ�ν��ڡ�1950����1957�귴��ǰ�α���ʦ����ѧ����ϵ���ڡ���ϵ���Σ��ĸ�����ڱ���ʦ����ѧ��������о�����רְ���룻�ĸ��Ժ�������ǰ�α���ʦ�������ѧ�о������ڡ�
�����������ҹ��绯��������Ӱ�������۵��ػ��ߡ�������ʮ����������ڴ��Ĵ�ѧ�����Ӱ�����γ̣�����ѧ��ӭ���Ϲ�ũ����ġ��绯����ѧ��һ����д����"һ���������Ϻ����Ĵ�ѧ������ѧϵ���������Ӱ�Σ������ҹ������ڴ�ѧ����ĵ绯�����Ρ�" "һ�������꣬�Ϻ�����ӡ��ݳ����˳����������ġ�����������Ӱ���������ҹ�����ĵ�һ�����ר����"ͬ���������Ͼ����������Ӱ���ίԱ�����ࡶ��Ӱ�������¿��������ҹ�����ĵ�̿����ʱ�����������������Ƚ��Ŀƽ�Ƭ���������������֪ʶ�����ڼ���л����������Ӱ�˺���������̣�ʹ�ÿƽ�Ƭ������������ߡ������ռ���Ч���ܺã�����ؿ��˹��˵��۽硣�������й���Ӱ����Э�����£��ھ��й�Ϊ�绯������ҵ�Ŀ����ͷ�չ�߳Ͼ�����
�����������������¹��ʽ����������1933������»��ʿ�Ƽ���������������ϻ�ɨä����¡�1934�걻ѡΪȫ����������������Ա�������в�ʿ�ʸ�1946�걻ѡΪ�й�����ѧ�����¼汱ƽ�ֻḺ���ˡ�1947����Ϊ�й�������ϯ���Ϲ��̿�����֯Զ�����������顣
������ս�ڼ䣬��ʩ����ʡ����Ϊ����Ӧ��ս����Ҫ�����������˲ţ���1941�����ڶ�ʩ����������ʡ��ԺУ������ѧԺ��ũѧԺ��ҽѧԺ��ѧԺ��1936��ͣ��ĺ���ʡ������ѧԺ��ǰ���ж������ꡣ����ѧԺ��1941���^��ʽ�ָ���Уַ���ڶ�ʩ���ɽ��ʡ����ͨ�������֪����ʿ���Ĺ�ȳ��棬��������������ڳ����ɲ�ʿ�ض�����ʡ������ѧԺ������Ժ���������ֳィ���ˡ�1942���ģ������ڼ������ѵ������£���"��·����"�ľ����ڶ�ʩ�������ɽ�£�����ն�����ڲ���һ���ʱ���������ɳィ�����������������ʷ�ء�Ӣ�ġ����ġ����֡���ѧ����ѧ�������Ȱ˸�ϵ�����������ҵ��θ�ϵ�쵼����ѧ������������������һ��У�ᡣԭ������У��ʦ���������������ž���ɽ�����Ҹ����������Ƶ������������ɽ�ڽ����Ʒ�����Ȼ�Կ�ʮ�����پ����������"�����֮���������Ž�֮����"��ÿ��һ��������Уѵ��������ʦ���İ���������ʶ���ɴ�Ҳ�ɿ�����������������ѧԺ�Ŀ��Ĺ��衣�ڿ�ѧ֮�գ�����ׯ�ϵĿ�ѧ�����ϣ���������������ѧ������־����˵��"��������ѧԺ���쵮���ˡ�������ʷ������ʱ��ʹ����ʲô����ʫ��˵��'ݼݭ��ʿ����������'���������ǵ������ʹ��������Ҫ��������������Ž����ˡ�Ϊʲô��������������Ϊ��������ӵ����ʮ������ʷ��ΰ���л����壬���ǵ�����ǧ����࣬��·���ڣ��������㣬Ϊ���Ǵ������ء��ҵ���Ӫ�Ľ���ɽ�ӣ����������տ���������������������֮�����̾���ʢ˥¡�棬��ȡ����������һ����������һ������֮��λ����Ϊ�ؼ�������ʹ����Ϊ�ش���Ҫ��۸ߺ�����ͬѧ������־�������ƣ�'ʿ���£�Ի��־��־���ڣ�Ի����������ƥ������'����Ҫ������֮�ǡ�'¥��ҹѩ���ɣ���������ɢ�أ�'��������ʱ�������������ˡ�"��ʫ�����½�εġ���ߡ���ǰһ�����½������ʱ����ˮ��������ĺ��飬��һ��������������Ĵ����ش�ɢ�ص��龳��
������ʱѧϰ����ȱ������Щ�γ�����û�пα����ο���Ҳ���赽��ѧ��ֻ������ʱ�����ֳ��ʼǡ���ˣ�ÿ���¿κ���ϰʱ�䣬�����Ǻ˶Ժ��������ñʼǡ�����ά�½��ڻ��䣬���꣬��Ժ��������������һ����������ѧ���м䣬Ҫһλ�ʼǽ�ȫ��ͬѧ�������������ͬѧ�Dz��䣬��Ժ�������ɣ���ָ���˹����س�¼������������ǽ���ϣ�������ͬѧ�˶ԣ������Ƹ����Լ��ıʼǡ���ʱʦ���Ĺ�ϵ������Ǣ��ѧ���ǶԳ�Ժ�����з��Էθ��ľ���֮�顣��Ժ����ѧ�������գ��������ͣ���������������ɳ������ֿ������κ����ﶼ������ġ�
����1935��1�¸���35��ʱ�ص�������������꿹ս��������ս����1949�����й����������ѽ�50�ꡣ��15�꣬�����긻��ǿ��ʱ�ڡ�����չ��ͼ�������ȡ���ڽ�����ҵ��ȡ���˲��ٳɼ��������Թ�ֱ��������һ��������������ϣ���ʦ�ѡ�ѧ�����ദ�ú���Ǣ������һ����������ˣ�����Ҳ���������������һ��Ϊ��������Ȩ������������ʹ���ڹٳ��к��ѳ��ڸ���ȥ�������ص�����ԭ���Ǻ�������������ȥ�������ڵ�Ӱ���ίԱ����˲���һ�꣬�ڶ�ʩ����ѧԺҲ������һ�ꡣ������У���顢�ڱ����������±Ƚ��ʺ��Լ������顣����Ը�����Լ���ѧ�����Ŷ������ڴ��Ȩ�������������ߣ��й��������뿪��ʩ����ѧԺʱ�����������ʣ���ǻ�������������"�彭֮ˮ�����ˣ�������־�����硣"��ʫ�䣬��ӳ�˸���ʱ�����顣����Ϊ����ȥ�������ڡ��������ɽ����ʡ������ѧԺ��һ�����������µ�������
����"�ұ���Ϊ���������ҵ�Ϲ�����֮־��Ϊʲôһ���Ժ�ȴ��������ظ���˳�Ϧ�빲�Ľ���ѧԺʦ���أ�����Ҫ����Ϊ������ϰ�������������������ɵ�ѧϰ�����������ڶ�ʩ���������պ��ϸ��ͳ�Ρ����磬����ʡ��������'�����'������ΪһԺ֮�������ȫ��ʦ�������Ʒ���ɽ���±����᳡����������Сʱ�����棬ʵ���˷�ʱ�䡣�糿�����ұ��뵽�����ȶ���������������Ȼ��Ҫ��������������ʡ������ϯ�³Ͼ�������������ѧ����ѧԺ�������Ź����ɽ����������Ų���ֱ���쵼���Ҳ��ܲ��ֹ��ʡ��������������̵��ǣ���������ֱ��������ѵ������ѧ�ţ�����ʵ��˼��ͳ�ε�����������;��½̹�����ɮ����Ħ��������Ҳ���ϼ������ģ�����֮��IJ���ì�ܾ��ף�ʵ�������ᷳ����ʹ����ȥ���ɽ�ĵ������ǣ���һ��ʡ����������ϣ��³Ϲ����������ѧԺ��������ѧ�����£�������������������ѧ����ʹ���ѿ������룬������������ʲô���������ʵ���������ܣ�һŭ֮�£����Ų��������ְ���ɡ�����������Ȼ�뿪�˺���ʡ����ѧԺ��"��ξ����ܳ�ֵ�չ¶�˸����˸�
����������Ȼ�뿪�����ɽ������������δ�ܰ��������ϵ���ģ���������ĵ��ǽ���ѧԺ��ǰ;���������ѧԺ����ܹ���ʡ����Ϊ�����������������Ͳ����ϼ�ǿ����ǰ��������á���ˣ�����������;������ʱ����Ϊ���¼������ߣ��õ���������λ��У���ر����Ų��ߵ�֧����˵��Լ�ͨ��ԭ��������ʦ��ѧԺͬ��������ת����ͨ���ڸ����뿪���ɽ����֮����ʡ������ѧԺ��Ȼ��һ��������һ�¸�Ϊ��������ʦ��ѧԺ����Ҳ�����dz�������Ŭ�������Ŵ˼�Ѷ������Ϊ���ˣ�Ϊ����ѧԺǰ����أ���Ϊʦ��ף����һ���˶��Dz�����λ����ı���������Ǹ������뿪��ʩ�������ı��ߣ�������Է�չ����������һƬ���֮�ġ�
������Ȼ����������ڸ���Ҳ�Ǻ����������ġ��������������ɵ�ѧ��������������涼����ʩչ������ʵ������չ�й�������ҵ�ij��ԡ���������ʦ��ѧԺԺ������������Ҳϣ�������������ʦ��ѧԺ���Ա㿪�����Ŀγ̡���֪ʶԨ�������й����������Ļ�����������ѧ���й㷺������о������������棬��ѧ���ݷḻ����ָ��ѧ�������Ķ�����ο��飬�������������ѧ���Ķ���ʼǣ������䷳�����ϸ�Ҫ��ѧ����ʹ��������Ķ������������������������ľ�������ͬѧ�ǿ̿�ѧϰ����˵��"����һ����ţ�ɳ�Ϊ��ѧ���ڣ���Ҫ������ʱ�̿�Ŭ�����ܷ�ѧϰ������Ҫ��ϧʱ�������飬��־�ȹ�����Ϊ���������˲ġ�"����ѧ���ǵ�ѧϰ����������ģ������뷽�跨ȥ�������ѧ���ǵ����ѡ�
����һ�������꣬�����㲥��̨��ʽ������������"����ѧУ"ר���Ŀ�������ɳ����ɽ��ڳ����ָ���ġ���ǿ�����֣���������Ĺ�ͷ�������ɽ��ڽ��绯����������"�ݼ��ǿ���Ʒ����ף��̾���������������"���������ߣ������㲥��̨�Ŀ�����ʹ������ʵ���Լ�����˼�����һ��أ���������ָ���£�"���ֽ�Ŀ������ʵ����"�������漰����֪ʶ����������ͥ����������档"����ѧУ"Ҳ����Ӱ�죬���ڷ�ӳ���á��������ڵ������뻶ӭ��"����ѧУ"�������壬���ݱȽ�ͨ�ף������һ�������˵���ڽ��ܡ���ս�ڼ䣬�����������Ǵ���ƽ����֮���۲졷��������棩����Ҫ����֮һ��һ��������ף���������һ����һ�Ұ�����Ŀ������ѧ����������ʹ���룬�߿���Խ��妱�д��"����Թ����Ǭ��������������ʳ��"��"����������ʿ������ͺ�������"�ĵ�ʫ������ʫ����¼��������ѧ������һ�Ű��������ġ�һ����һʫѡ��֮�У���֧�ֽ���ѧ���˶���������ǿ�ҡ������İ�����
�������������ʱ������һ�������������������ۣ���1944������ˡ������Ľ����������죺����ӡ��ݣ���
�������й�����ǰϦ�������彫���������Ϻ��������ټ�ʮ��λ��ƽ�Ľ���ѧ�ߡ����������������ӭ�ӽ�ž���ƽ��ű�ƽ�����⣬����ҲӦ��ǰ��������Ļ����챯�衢�����µ�����ѧ�ߡ������һ��ͬ���ƽ��ű�ƽ����ӭ��ž���ǡ�
����1949�꣬��ʷ�ҿ����µ�ƪ�¡�ʮ��һ�գ��л������ĵ�һ������ڵ�ҹ�����̻�����ҹ�գ��������������֯����һ����ʵ�ͼ����������ҹ�մ���û�й��������������財�ȫ�ǵľ����ڹۿ����յ����̻�Ĺ���ӳ��������һ���˵����ϣ����ս��˸��������������ǻ������Ϳ�����ҪΪ��չ���й��Ľ�����ҵ�����˲ţ���ͬ���������ŷ�չ�����������ͼ����������Ҫ�Ǹ�ְҵ�����Ļ����������ͺ����θ߽̲���������������������
����������µ�ʹ��������Ŭ��ѧϰ����˼�������壬ѧϰ�����������ۣ�ѧϰ����ڷ�������������������������Ҫ�Ĺ��ס���ʹ�ڱ�����Ϊ�����Ժ������β��������������������������ϴ��������֡������������˵��ֱ������Ҳδ������и���������ع�֮�����ѳ������Ҫ���ߺ������У����й���������֮�Ľ�����������������Ӱ������ͼ��ݡ�����ʵ��ѧ����ϰ��������ʵ����ѧ���������������Ľ�����������������ѧ�������룩������������ʷ�����������������ҽ���������ѧУ�����������룩���������Ρ������룩�����������С������룩��������������ѧ�������ߵ�ѧУ���η����������룩���������о������ݺͷ����������룩������������������ѧ�������࣬1982�꣬������ѧ�����磩�ȣ���Ϊ�������Ӵ�ѧ���ࡶ����ѧ����1985�꣬������������磩�����������Ľ��������о���������������Ľ�����ѧ�������Է�չ�ҹ��Ľ����������˺ܺõ����á�
�����������йɾĹ�ֱ�ˣ�����������ʲô����˵ʲô���������ˡ����������˱�����һ��֪���ԡ�������������������ʱ��˵����������ר�ҵĻ�Ҳ�������ţ�����һ�ж�����������һ�㣬�����л����壬�ӿ��ӵ�����ɽ���Ӳ�Ԫ�ൽ�����࣬������֪�����Լ����㡢�ƾõ���ʷ��ͳ�������Ľ�����ѧУ������Ҳ��ֵ�����ǽ���Ķ������������Ļ�����һЩ����������������ɡ�������������Լ����������գ������ֱ����붨��"����"������Ϊ�˷�չ�й��Ľ�����ҵ�Ÿ���������ġ������찤���������Զ�������ֻ��һ��СС��Ҫ��"ǧ��Ҫ����Ů��������"��ʱ�Ҹոչ���ʮ�������գ���һ�����ж��꼶ѧ���������������ССҪ��ʱ�Ҳ���֪�����������ϴ�ѧ�Ժ�����һ��ѧ�������ҵġ���ô�ɾ��ĸ��װ������Լ�ĬĬ���ܾ��ʹ��������ʱ�����ڹ��İ����Լ����ٵ�Ů������Ȼʱ�����꣬ÿ���估���£�����м������ᶼ����ס��ӿ�������������ҿ����ˣ���С��������ܲ�ס�����Ҽ�ʹû�п�����Ҳ��ƾֱ���е������εij��ص�ѹ�֡������������ҲŪ�����ף�����������һ���ٻ�����ĸ��ף�Ϊ�˰��Լ������������һ���ӽ��������˳�ǧ�����ѧ���������������ɣ����Ż����Ѫ���������������ô����һҹ֮���ɷ���������ĵ����أ�ֻ�����������ף�ĸ�ײ����������ף����ȴ�ǰ���������ˣ��Լ�������ʳ���ø��׳Ժ�һ�㣬�Բ������ǹ������ۿ�������塣
�����Ļ�������У�����Ȼ�������⡣��������סţ�ɨ¥��������ÿ��ֻ��һ����ʮԪ����ѣ�����ʹ����Ҳû����������������
�����ĸ���ڣ������Ĺ��Ʒ����ˣ���ȻҲ�ֵ�һ��"����"��������û��ǽ�����쵽��ȫ���źʹ���������һ��ɹ̨����֮���Գ���Ϊ"����"������Ϊɹ̨�ǹ��õġ���ůʱ��ʲôʱ����ȥɹ̨���·����ϰѣ��캮ʱ��ȡ���������ʳ����˾Ϳ����Ŷ��룬�������Ŵ��к�������ͬ�����Ŷ��������㡣����˵��֮ǰ�������Ƕѷ����Ρ�ɨ��������ĵط�����ʱ����һ�ŵ���ľ�崲���ͱ���˸�������֮�����������������ס��ʮ�ꡣ���죬��Ȼ������ĸ���þɱ��ַ��Ƶ�˫�㴰���������ﻹ�����Ҫ���������线���Ź���������ö��������ߺ��ϱߵ�ľ�Ű�ʹ���������˲���г�ı��������������죬�����ڶ����ɸ���ȴ�������µظ���䶷��ȡ��Ϊ"�����"����"���"������Ȼ�ǽ���³Ѹ�Ķ���"��ü���ǧ��ָ������Ϊ����ţ"�����ӽ��Ͱ͵�������м���Ǯ������������ɫ�����СС�������������컨�壬����ȥ��Ҳ������Ŀ������֣�������ʲô���ش���Ϊ������Ӳ����������"�ǿ�"--������Ȼ�Եõ��о���������ϵ���ˡ���ȻǮ�����ã�������ÿ����һ����Ʊ��ֻҪһ�°࣬��������ת�ơ���������Ҳ������ȥ����ʱ�����۾������ü��������ʼ�į��Ҫʹ������ﲻ�ϵؽ���������Ұ����Ѱ�����������ǫ�ľ����ã���������ȥ���������ʱ�ڵĽ��ã������ܿ���չ�������������ڽ���ɢ��ʱ�ͺ���ũ���죬����֪�����ǵ�������ô��������������ô�롣����һ��������յ��ˣ�Ω����ˣ��Ų��ᱻ���˵Ĵ����Ƴ�������
��������ʮ��������������У���ɥʧ���Ͻ�̨��Ȩ����ɥʧ�˳����Ȩ����ɥʧ�˺����ѽ�����Ȩ�����Һã��������Ͷ���Ȩ������Ȼ�����Ͷ����ڱ����ķ�Χ�ڡ�����һ��˵��������һ��רְ�ķ���Ա��һ����ѧ������Ա����ֻҪ���������빤����ȥ���������Լ���ר�������������á�����������֣���Ȼ���ǰ������������ȥ����������һ̨�ܺ��õķ����������Щ��������Щ�Ͷ��ɹ��ĺ�ѧ�ǣ�����˵��������������ԭ���ߵ�л�����ҶԴ˱�ʾ��ƽʱ������Ȱ��˵��"ֻҪ�Խ�����ҵ�кô�����Ҫ�ƽ���Щ��ë��Ƥ���˵��ػ�Ӧ����һЩ��"
������Ϊ����������ۣ���ʣ������Ĺ�״��Ұ��Ҳ����˵���������Ķ��������һ���ձʹ������⿴��ֻ�ܿ���һ��㣬����ҽ������ȫ�ݡ���д�ֿ����Ѿ��dz�������Ϊ�˿������������һ�ٶ�ʮ�ߵ�ǿ���¹�����һд���ǰ�ҹ�������Լ����۾���ֱ����Ű���ij̶ȡ��쵼������������ʱҲ߯����һЩ������������ȥ�ۿƾ�ҽ��ҽ����������˵�������������ܸ���һ��������Ҳ���ܵ�ʱ����ȫʧ��������������һ��ʱ���ڻ��ʹ�ࡣ����Ȼ��������������Ȼ�������ϡ����Ϊ��ȡ�ü��������ı�Ҫ������������ð���գ�����ʹ�ࡣ�������Լ�����ס��������ľ�ʹ����̸Ц��������ͬ�����������˽����£����������ֹ����ϡ�
����������Ӷ�������������ʱ����ͬ���õ��˽�š�Ȼ�������ȥ������˫�ۣ�����ȫʧ���ˡ���Ҳ�����й��м���Э���һԱ���Բ�������ʮ�����ģ�����һ��ľ������Ǽ��������Ӧ�������Ծ��˵��ٶ���Ӧ��ä�˵�����ճ�����������ȫ�����Լ���������һ���������ɹ��ˡ����Ѷ���Ů���������ٵ���С���ȡ���Ը�Լ��ĺ���������϶�����������Ϊ�����ġ�
���������ں������������ʮ����Ŀ��������������η���ĴݲУ������������ŵı�ʹ��սʤإ��Ŀä����ࡣ�ڴ�ĺ֮�꣬ƴ����������ȥ�����δ����ʹ������д��������Ҫ�Ľ�����ѧ�����������������Ѻ����߷����ʵ�ѧ���߷�����ݣ�����������ȵط�չ����Ϊ���������ҵ�Ķ�������ֻ���Լ������࣬������Ϊ���������ҵ��������һ����ע���������ҵ�ķ�չ���о��������ۣ�����Լ��ļ��⣬Ϊ�й�������չ���ײߣ�����������֪���ԣ�������������һ���ӣ�ֻ��һ��־����Ϊ�й�������ҵ�Ϲ����ᣬ��������������������ڡ�
��������һ������������д�³���ʫ��ʮ�ס����䡶��־ʫ�������䣬���Լ��䱧����
����˼Ϊ�Ļ���ש�ߣ���Ч��ä�¸��š�
������ʫ�ƽ��ֶ��٣�׳־��ֿ²��
�����������漯ͯ���������������ġ�
��������ʷʫ��ıʳ�����������Ϊ����
�������ʷ��������Ըʤ��ϲ���ࡣ
�����þ���ֻ�ƻ�ã���������Ϧ������
�����������������ݱ��Ϧ���䶷�����ţ��Ӳ����ϣ�Ը���³������������ס�
������ʮ���ĩ�������αȽϽ���ѧ����ʣ���ʮ��������й��ߵȽ��������о�����ʡ��й�����֪�о�����ʣ���Ϊ�о���д���ģ���ı���ߡ��ĸ����ѡΪŷ��ͬѧ���������᳤��
�������׳��������⣬�����о�������Ϊ��ѧ�������Է������͡�ֻҪѧ��ѧ���汾�죬���ͱ�ʲô�����֡��ĸ�����������о����У��Ⱥ��в�����������������˲�ʿѧλ���������ѧ���У�Ҳ�ж�λ�ڹ��������ѧ������쵼��λ��
�����������������ڼ����ڿΡ�Ϊ�˽̸��о�������ͼ�����ϵĸ��ַ�������������������ͬ��������ͼ��ݣ�������˵�һֱ������������㣬�Ⱥ�Ŀ¼�ҡ������������ҡ����������Һ�����顣���ļ������õó��档����ǰ������ij��ͣ���Ȼʱ����ʮ�أ����������һ����Ȼ��Ϥ���������Ѯä������ָ�ӣ�����ѧ��Ӧ�õ��ļ��ݡ��ĸ����ӡ��ĸ�λ�ò�����Щ���ϡ����������ڽ��ϵ�С�Ե���㶫���伢��Ȼ���ڹ���������Ϣһ���������һֱ�ܸߡ��о������˷ܵ�˵���ͳ���������һ�Σ�ʵ��ѧϰ��Ч�ʵ�����ͼ��ݣ��ջ���ˡ�
��������ͼ���������Ϥ��������ʷ��Դ�ġ���ʮ���Ͷ�ʮ���������������ͼ��ݹ�������һ�������������������������ӡ������ζ���ͼ��ݹ���Ա���ڶ������ں�������ͼ��������IJ����Ρ���ڶ�����ְ������������ͺ���֮��λ�������㽭ʡ�����Ƽ��ġ�������1943��������������������С���顶ͼ��ݡ������ݾ�Դ������ͼ��ݹ�����ʵ������Ͷ�ʵ������Ŀ����о�������ȫ�潲����ͼ��ݺ��������Ĺ�ϵ��ͼ��ݵĴ������������ѡ��ִ�ͼ��ݵķ�չ���Ƶ����⡣��һ���Ȱ��鼮�������й�ͼ�����ҵ�ķ�չ����������ͼ��ݾ������顣���ڶ�ͼ���ѧ�Ĺ��ͽ�������������ѡΪ�л�ͼ���Э�����¡�
��������������"���ϣ����������䣬��ƴ��������Ϊʲô�أ�"����˼Ƭ�̣��ش�˵��"�����������ĵ������Ž�����ʷ����������֪�����ڴ���������֮�У��Լ���̫��С�ˡ�����������֮�飬�ر��ǵ����˽��ʮ���������л�������γɺ�����ΰ���ף�ǿ�ҵ������Ժ��кͰ����������������ĵ���Ȼ�����������л���������д�ͬ�����룬���ÿһ���о�����й��ˣ��ر���֪ʶ���ӣ���Ӧ�����⣬���Ϳ�����������㣬�ǹ��������������㡣ֻ��Ϊ�Լ������ţ��Ǻ�������ġ�������������'Ϊ˹��������Ϊ������̫ƽ'��������κμ�������;�����ʹ�����ɥ����"��������������ָ������һ���ĵ�·�������ⴣ�������֮�������ʹ������������˳�������澳�����ܴ���Ӧ�ԣ����Լ���ɵ��¡�
����һ�Ű���������һ�գ��ΰ���ȥ����ĸ��������ĸ�ײ���ʮ���ꡣ�����ߵĸ�����һ�����صĴ�����ҿ��ó�������������ڱ�ʹ֮�С�����û�б�ʹ���۷�����ѧУ�����˸���ο��ʱ����л��֮��������̸���˹�����������һ������߲�Ρ��߾��硢�������������ˡ������ɵ�����������������и������Ķ������������������������������Գ���֮����Щ����֮�¡��Զ�ʮ��������ͨʦ�������ʦ�����ʮ�����£������顢���顢���飬δ������и����ʹ����ߣ��Ϳ����������������Ƶ������������Ļر����������������
�������룬��Ҳ�����Ǹ��еĵ��º���ٰɣ���Ҳ�����������������������Ծ�������л���ĵ����ɡ�
�����������ڡ�ʫ�������˹�������Լ���ʫ��������д����"���ںڰ��У�ȴ�ѹ���������ѧ�������ǵĵ����ô��Ҫ���������ˣ�ǧ������£�"
��������ѧ�����������������������һ����"�ǻ��������������ֽ�ѧ��ʧ������������ڹ��ɳ��������״��绯������������������������ȽϽ�������һ����ǧ��"��
����������ҵĸ��ף�һ���ӿ��ѵ�ĥ�����߹��������ˡ������ݵ����ݺ��������ǻ۹�â���۾�ʱʱ�����Ժ��и��֡�����һ�ĺ�����ɤ�ţ����������ң�"��������������ջ���"��Ҳ������ʵʵ�ػش�����"�ǵģ��ְ֣��ҽ����������֣���һ����ջ�"
����һ�Ű��������ʮ���ճ���
����������һ����¶�ʮ���ն���
��������������һ������
������ţ�
��������
����Ҫ��
�����Ƽ�
������������ˮ���乩ů ���������������ů
�� ������ӭ����ý�塢�����硢Ӱ�ӹ�˾�Ȼ����뱾�����г��ڵ����ݺ�������ϵ��ʽ��027-88567716
�� �ڱ���ת������ý������Ϊ�����������Ϣ�������������������۵㡣�������ת�صĸ���漰���İ�Ȩ������Ȩ�����⣬�뾡���뱾����ϵ�����������չ�����ط��ɷ��澡�����ƴ�������ϵ��ʽ��027-88567711
�� ����ԭ��������Ϣ������ȷ�����Եı�ʶ��������������������"������"��Դ������ת�ط����Ǿ�����ԭ����������Ϣ����Ϊ�����������䷨�����ε�Ȩ����
�� �ڱ���BBS�Ϸ������ۣ�����������������Ӧ�����ԡ�������������ط��ɷ��档
对不起,您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已被删除!
10 秒之后将带您回到荆楚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