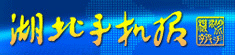�ƶ�
����ʱ��: 2009-11-23 17:10 ��Դ: ������ ������ӱ�
������/����
�������ҹ���¹��ɭɭ�ġ�
���������ڼ��ж��������˴���ͷ��ûϴ�������������ƶ�����Ѹ������ȥ���������������ݵ���ʱ�һ������������һ���μ�һȺ������ɫ��װ������ս����Ҳ�����������ģ���Щ����Ҳ���Ѳ����Ǹ�խխ��������Ȼ��ͽ������ĺ�����������ϣ�Ҳ�����Ǵ������ӵ�����������ӵ����õ��˿����������ļᶨ��׳�ҵ���ȥ���������������ˣ��Ǹ��״�����ⳡ"ս��"���ҷ·�ǵ���һ��Ҳ�����������Σ���������һ�ε������������ġ�
�����ҹ������ݵ���ʱ������˵��"��ţǣ����Ժ��"
���������Ҵ����ڿ��ȥţ����ǣţ����û�뵽Ҫ���·�����Ϊ�һ���Ŭ�������Ź��µĽ�֡�ţ�������Ӻܶ࣬������Ѹ�ٵ����˺ܶ��ɫ��С��������ţ���͵ij�����ڵ��ϵ�ţ��������ţ��ǣ�������Ӿ�������һ����ӵ�Ÿ��˳�����
�������ʱ��Ĵ����ǰ����ġ����ڵ��˼��Ѿ���ҵ��سǣ���Ժ�ӵ���ľ���Ӳݶ�����һ�𡣰�ɭɭ���¹�����������һ�㱡������������һ��������ȥ�ı�����ȥ�����̡����̴��������ӳ�������
����ǣ��ţ�һ��ݼ���˯�������ڴ��ϰ����ĵȴ���һ��ߺ�ȣ�"�����ӣ�������ͷ֮�����㣬�����Ľз����DZ��ӣ�������"ߺ������ɳ�ƣ�������һ�㣬������Զ����ʹ�ڼ�ʮ���������ﶼ����Լ���������dz����С�̷������������ġ���ʱ���Һ�С����Ը������ߴ�����������ũ�˳������ˣ���Ϊ����ڴ�����걾ʽ��ũ����˵�����Ǽ������ģ����������ǵ�ߺ�����������ɣ�¶����Ȼ��Ұ�ԡ�
��������������Ҳ��Ҫ�ֵصģ��������͵ü���ʱ�����������������������������������糿Ҫ�ȵ��ˡ����ڵ������¿�����һ�����Ҽ�����ߺ��������Ȼ���ٷɱ������ӣ�����Ǯ�����ӵ������ó��Ⱥ��������ӡ�ÿ���Ҷ��dz�Ĭ�Ŀ������ƶ���˫�֣���������ҪЦ��һ�������ƽ���"������"���ҵij�Ĭ�Dz�֪���������ƺ��������ĸ������ҵ�үү���DZ����ˣ������е����Ĩ�ǵĹ�ϵ��������һ���㲻֪���������ƺ�������Ҳ���Ŵ��˽��������ӡ��Ҳ��������ԭ����һ�������������ϳ��������ӣ��������Ǻ�ϲ��Ц�����ܲ���ȥ��������������Ƭ��������š���ƫƫ���������������Ǽ�ϲ���ģ��Ҳ�֪��ÿ���峿�������ڵȴ�������ж������ڵȴ�����֮����С�����糿��һ���羰��
��������ʮ���ʱ�������Ѿ���ʮ�����꣬��Ȼ����һ�ֺ����ӣ�����ҲӲ�ʣ����ŵ�����·������ꡣ�����֣���Ҳ�֣��Ų�ȴ�ƶ��Ŀ죬�������̳���ʱ���������������صĺ�������
�����ٴ����ڴ��ϣ�������˯�IJ����ȣ����Ժ����������ְ�ɭɭ�����������̵������Ҽ����ر�����������������һ��ߺ���ܾ��絽�������������᷿��ĸ������������������������ʹ����������ʱ����Һ�������������һ��ʲô���IJ�����ĥ����ҹ�����¡�����ȥ��ο����ȴ��Щ�ķ������뵽�����������ջ�ļ���һ���˳е�����Ͷ�����
�����Ժ����ҼDz�����ߺ��������ǰ��������ʲô�����뵽��ʲô��������������ϲ�����������Ҵ�������һƬʱ�Ҹо���ߺ����һֱ���Ҷ��ϻ��죬��������ʱ����������������е����Ҷ������������ץ�˼��·��ͱ������ݣ������������������Ŷ��ص������һ��ɻ�����������ʶ���ʵ�ʱ��������Ҽ���ǰ�ະ�˼�ɤ�ӣ���Ϊ���ҳ���ʱ���պ�վ���ҼҺ̳����롣��Ȼ����˵��
����"�����ӣ�������ô��һЩ��"
������������û�лش�������Ĭ�İ����Ǯ�ݸ��������������İ�Ǯ�������ӿڴ����װǮ��ʱ�����Ǻ��������ܿڴ������Ǻ�������Ҽ�����Ը�Ŀ�������֫�ϵ��⣬��������������������֫�ķʺ������������ʱ��Ҫ�������ӡ�Ȼ��������Ҫ�����µģ����ƺ��ܴ��ġ�
����"����զ����ô�ࣿ"�����ʣ�����û�ش�ĩ�����Լ��ش�" ���Ǽҽ����ջƶ����������˶̹��ˡ�"��֪�����������ǹ����ʵģ�ÿ�����ʱ�����������ҿ���˵��������û�������ó�һ�Ρ�����Щ���⡣
��������������Ǯ�������ӣ�Ȼ���ٺ����������ŵ����ߡ�����Ҳ�������ڻ��ݣ����ƺ���ϲ�������ı�Ӱ�ģ�ȷ��˵��ϲ����������������·����ʱ���ұ�������Ǵ��������˵�ǿ�ߡ��ҳ�����������������Ľ��������������Dz���������ү���ƹܣ�
���������������������г�������ĸ��ס��Լ��̹�����ȥ���̹�Ҳ������ͬ��ĸ�Ů�����Ǽ��е��Ǹ����˻ƶ����е��ǻ������ո���������Լ�����Ŀ���ʱ������顣�̹���Ҳ��һ������ڵ���æ���û���緹���������ǰ���͵ij�ʳ�����һ����˵��̫���ڿ�����û�Ǯ�ȵȡ���������Ȱ˵�����Dz�����һ�ѻƶ����ϳ����������Եļ���ϸ,�����DZ�����������������ϡ�
������������һ�Ҫ�ؼ�ϴ�·�����ú¯����
�����ҵ��Ƶ����ɱ����﹣�ϣ��﹡���Ǻ�խ������·�涼��������ݣ�ֻ���м���һ���͵�������һ������·¶����ɫ����������ͯ��Ļ����˵�������Ѿ�ϰ��������Ƶĵ����ɱ���������"����"�ϡ����ǵij��о���ÿ�����طɱ���������"����"�ϣ�����ѧ����ææ�ؼҳԷ������˷��ּ���ææ��ȥѧУ��������Ҳ�����⡣����·�ϵ�ʱ�����Ժ����ܻ�ij�³Ѹ������һ�仰��"���ϱ�û��·�ģ��ߵ��˶���Ҳ�����·��"
���������Ķӵ�ת�䴦���˸���ɲ�����������Աߵ�������������ȳ��ŵ�����ҵ��ȶ�ֻ�ÿ����³�������һ�ߣ��������������������ͨ�������忪�������ļ������������ܻ����ϸ�Ŀ�������С�ĵ��ƹ�һ���������������ٿ�������һ����������ӣ������һ���������Ƕ������������ˡ�
��������ļ����ܺã���������ũæ��ʱ����������ת�����﹡�ϡ�������Ѱ����Ҫ���˵����ˡ�
����������Ҳ�������ˣ���������ʲô�������գ�ר����С����Ķ����������ʱ������һ��С�������ҷ��������С�����������ڵ��ϻ�����������������塣�����ǰ�������Ϸ���������ܻ���ִ�������ࡣ�������ǻ��������ľ����³��֣��Ի������ǽ��ŵ����档��ʱ����������ͯ������������Ŷ���ʽ�Ĵ����г���������ÿ��ÿ���ĺ̳�ǰ�����Ķ������г��Ϲ����˸�ʽ������������˵�ĸ�ʽ���������ǵ�ָ�������ɫ��ͬ������˵����������죬�е���ƻ�����е���Ѽ�ӡ��е���ëë�桭��������Щ���dz���������֡���ʱ����һ����������Ǹ��������ɵ��ˣ������ǻ��кܶ��������С����ע������Ȼ�����Ƕ��ֻ���۲��ſ����Ӵ���ͷ������ͷ���������"����"Ϊ�����γ�һ���Ӵ��ϵͳ����������Χ����������ҲΧ�������������ƶ��š�
��������Ķ������г��ͻ����ӵĵ���һ���Ǵ���ķ羰��
�����Ҽǵ������������һ������ġ�������������Ҫ��ĸ�������ĸ�ײż�����Ը��������ëǮ���ҡ��õ�Ǯ��ʱ�������Ѿ����˺�Զ��һȺС����ӵ�����ϵ������壬��ϸ�ĵ���ѡһֻ���Ŵ��ǵ�"����"������ͷ�����Ӻܿɰ���Ȼ����û�кúõ���ϧ����"����"��С����ǵ���������һȦ���Ҿͽ��������������һ����Բ����������ѧ����������Ӱ������"����"�����ӣ��������ܰ�������������Dz�������ô�䶼�䲻���������°�����Ū��ԽŪԽ������ȥ��ĸ�ף�ĸ��һ���ҰѸ������������˾������Ǹ��ܼ��ӡ�����ĸ�װ�������"����"��ĸ��˵�Ҳ�����ȥ�����塣�����Ҿ�ȥ�����壬������˵����ȥ�������Dz���ά�ģ�������������Ǯ��Ҫ��Ȼ����Ǯ�ˡ���˵������ֶ������Ӧ�ð�æ�ġ�����˵ֶ��Ҳ�����������Һ�����˵����ʱ��������������ͷ�����ջ��������棬�����������ȳ�ˣ�����������Ħ�����̶������졣��ͷ�����̲�ͣ�Ŀ��ԣ������ջ���ӽ���ڲ����������ơ������ϱ���ͷ�Ƣ���ˣ�վ�����ݳ��ջ��ݳ���ɤ�Ӻ���"����Ѭ����ѽ�����̻�Ѭ������"�Ҽ����"����"������ת�����ؼң���������һ��µ���������ݣ�Ц�Ŷ���˵��"��ʱ�䳣���氡��"�һ�ͷ����������Ц��ȷ�ÿ����ֲ��ù��յ�����ҪȢ�������š�
�����ұ��Լ�����һ�����Ҳ�֪���Լ���ô�Ͱ�����˵�ɹ��յ��ˡ��ѵ���������������������������ǰ�������е������������Ϊһֻ�������ƻ��ˣ��Ǹ�ʱ������ѧ����һ����ȵ��ˣ����ҷ����������ˡ�Ҳ���������Ļ����������������뵱��������������һ�Ų��ƣ����ұϾ����Ǹ�С���ӣ���û�����������ߵ�������Ҳ�Զ�������ɼҵ���˶��Ա����������һ�Ž�����Ǽһ�����ҵĺ���֮��һ���ᱻ�����������һ����������е����塣�ɵ��һ�ͷ�����������Ѿ������ˣ�Ҳ��������û�����ҵĺ����ٶ���Ҳ����������ʱ���������������ƨ�ɽ����ݡ�
�����������������
�������ȷ�Ǻ��ˣ����ǿ�ʼ�����ˡ��ҵ�������ʼģ�����ѹ��ҵĺ����ٶ�û���˷�����������һ�������������˵����硣���DZ����Լ���Ӧ��ѡ��һ��������ʱ�������ʱ��Ĵ���æ��һ�죬Ů������ƣ�����������˵���������������������̶��ں�Ժ����ţ�Բݵ��ų�ʳ����ţ�Ƕ������˵ģ������˲���ҪŮ��ʱ��ţ��������Ψһ�Ļ�顣
����������һ�վ����˶��ԣ��Ҽ�����Ը��ڣ���Ϊ���ƻ����ҵ��ж�����ϣ�����������̳��������ҿ������ϵ�������Ƭ��Ȼ������û�У���������ĵ������ˣ�������Ҫ�������Ż������
��������һ�λ���������������Ц�����ſɰ�������ӳ���˺�ɫ�������
�������뿪��˶�ؼ�ʱ��ֻ�������ŵķ��������������־�ļ�С�ԭ����һֱվ����˶��Ա��⼸ֻ���ŵIJ��һ�����������ʹ���������˳����������"��辫���ģ��㺦��ȥ���ģ�"���������ɣ����������������������Ѹ����ʧ�ںڰ��
���������Ǹ��˾������������������������س�����һ�˵������Ҫ�뿪������ġ�һ��������Ⱦ�ʱ���������˵��
�������뵱�����ٴ���������"����"�����̳�ʱ�һ����������С������м�������мһ�˵ı��顣Ȼ������û���������ˣ���Ҳ���ٿ������������﹡��ת���ˡ����ƺ�������ʼ����"��ũ��"�ƻ��ˡ��ҵļƻ���һ����ա�
�������ǼҵĻƶ�һ���������졣��Ϊ�����������ƶ�Ҳ������������Ȼ���ڵ��Һ��������壬���һ��ǻ��������������������������˻ƶ�������һ��Ϳ��Խ�����ɻ����չ��ǻ��롣��ʵ����ǣ�Ż�ţ�������ƹ��Ű峵�Ѷ���һ�峵һ�峵�����ˡ�
�����ڶ������ǻ���������������������������Լ����������ġ�
����ĸ���������õ�ʱ������ͽ������Ǽҵ��š������ĸ����⣬���һ�����϶���Ц��˵��"�����������ˣ������ѣ�"�Ҹ����Ǻ����������ȾƵģ����ϾͰ�����ꡣ��������ȥǰ��ȡ�þ������ҿ���һ�����壬���廹��һ����Զ��Ц�����ӡ������˸��Ļ�ȥǰ�ݣ�����û�þơ��ҲŲ�������þƣ�ĸ�����ϰ���ȡ�����ƣ������ջ��ݺ�����ƫ�Dz�Ӧ��ĸ���Լ���ȡ��,�����Ǹ������ò��졣ĸ��������������Ҹ��ᷳ����֪�����������һ�������飬���������������ŵġ�
�����ҽ����ݵĵ������Ҿ����ںڰ�������ջ�����ĸ������塣�ջ��ݵĵ���Щ���������ϻ����˻ҳ���֩��������ֻ�����ĺ�è������ú¯��������Ŀ������ϵIJˣ�Сè���ڵ��Ϸ����������ȥ����ͻȻ��Ц����Ϊ��ʱ����ı������ֻ�Ϻ�èһ��������רע�Ŀ��ű�����ľơ�
�����������ں���һ���Ʋ�����˵���˴��е�Ŀ�ģ����Ǿ�����˼���˲����������ִ���һ�ֵ��ĵ�������"�ϳ�����Ҫ�ڳ��ィ���ӡ�"
����"���Ǻ����ۣ�"�����žƱ�Ц�ˣ�����Ц������������˿��ǵ�̫���ˡ�
���������ֳ�Ĭ�ˣ������Ͳ�ס�����ˣ�"��ɶ�����˵�ɡ�"
����"��Ҫ������ݣ�"
����"��������ͬ��ô��"����һʱ���뵽��������⡣��Ҳ��������ͬ�����ĵ����⡣
����"��ͬ��Ҳ��ͬ�⣡"��������������˾��ġ�
����"���������а���ô��һ��ȥ���"
����"������һ���ջ��ݸ����ϰɡ�"
�������������������������˼��һ��ͷ����һ���ƣ�����һ���ƣ�˵"�ã�ɶʱ��������һ�����У�"
����"����Ͳ������ҿ��������������˻ƶ�����ϱ��Ҳ����æ�"����˵��վ����Ҫ�ߣ���������������˵�ٺȼ���������ִ��Ҫ�ߣ�����Щ���ˣ��Ųȵ���Сè��צ�ӣ�è������˺���ѷεļ�С��Ϻ�è�ø�����������ŵĵ���Ѹ�͵���������������ϴ���ĸ��ӦҲ�죬�����е�Ĩ���ӵ���è���ϣ���������һ������ôЩ�꣬���Ѿ�ϰ����������è����Ϸ��
�����ڶ��������Ȼ�����������������������ǼҵĻƶ��ء����忪����Щ�������ײ����ƶ�����̫�š�̫�������ո�ļ��ھͻ����������Ұ��������ո�ʱ��©�Ļƶ������˲�ע��ᳶ��һЩ�ƶ���
�������彫�����������յ��ϣ��������ڼ�ʻ���ϵ����Ǹ���ƶ���һ��һ��ı��ϳ���
������Ȼ������ʱ�ڣ�̫�����Ǻܶ�����������������ͣ�ĻӶ�������������ɳɳ�����졣һ˿��Ҳû�У���ˮһ���ӾͰ�Χ���������̵��۾����ۡ���ʹ��Ů�̹����������������½�������ϵĺ�ˮ�������ɱ�����Ӿͱ�¶�������¡�
���������ٽ������������������һ���ܺÿ��ĺ�ɫ���£����·��������������ĺ�ϸ����������Ƥ���ͺ�ɫ���������γ������ĶԱȡ��ҵ��������ᵹ�����
����������Թ���������䣬˵�������æ���������Լҵ����ݡ��������������壬�������һ��ˮ��������ƶ�����ô�ȵ��춮�õ��������ׯ���˻���Լ����ľ�������Щ�����������촩��һ��������ϲ������ţ�п㣬������ʱ��ƨ�ɾ���ϸߣ���һ���Ӳ��ʯͷ��Ȼ�������ƺ�ûע����Щ��Ҳ�ѹ֣�ũæ��ʱ����˭��������Щ������ûע�һ�Ե�������������͵͵�Ŀ�����
���������Ǹ������ˣ���������Ҳ����ĺܿ졣
�������ǻ�����������һȺ�ȳ�����Ŀ�����"Ұ��"��
���������Ͼ��Ǹ����֣�ֻ����һ���վ�����������ͳ��ÿ��������ߺ����Һ��ź���û�������½��������Ȼ���Ľ����������ò������ģ�������Ҳ���ܿ�����Բ������ӣ���Ϊ������ũ�帾Ů���������֡�
���������ָ���һ�����Ұ�ˮ���ù�ȥ��ˮ��ũ��ũæʱΨһ�ܻ����������Һ������������ˮ������һ��һ��Ŀ����������Ҳŷ����������������������ͽ��������������ĺ��������������Ӿ�������һ����������������"����"�ε�����Щ�Ļ����ҡ�
���������·�������ʵ����ˮ���ܻӷ������ı���ʪ��һƬ����̧ͷ����ʱ������Ҳ��һ������������ϡ�
����"Ī����Ҫ�����˰ɣ�"������ʶ�ĺ���һ�䡣���������ҵĺ������쿴�����ƣ�˵��ʱ�����¡������Ÿ��Ļ�����Ϊ�����Ǹ��걾ʽ��ũ���������Ƹ������а��յġ�
�������Ǵ�����ﻹ������һ��ʯͷ����Ҽӿ��˽��ȡ�
���������ʱ���������������������������Щ���ⲻȥ��˵����IJ���˾Ͳ��ͷ����ˡ�������˵�Ҽ���Ҫ��������ˣ���һ���˾Ͷ�һ��������˵�žͻ�����������������û��˵ʲô������֪���������������ø���Ȱ�����Ӳ�Ҫ������ݡ�
�����������������ȷ�˵ĺܿ죬����Ҫ��ʮ���������˵Ļƶ��������ˡ����忪������������խ�﹡�����ص����ţ��ƶ��ں����϶ѵ��ϸߣ������ж��ķ��ӡ�
��������Ҫһ���Ϳ���ȫ�����꣬ʱ����������ĵ㡣˭��û�뵽����ô����չ�����Ҷ��ڵ���ȴ������������������ȥ���ϰ��컹û�����������ӽ����ֵ�������������֦�£��������û���������ˬ������ȴ���磬���һ���Ũ�Ҵ̱ǵ�ũҩζ�����Ż����ӵĹ⾰�Ҹ�����ȥˮ��������ûЦҲû��ˮ������Щ�����ҵ�һ�ζԻ�������ô�ÿ���û���顣
����������ͣ���ò�ñ���ŷ磬�����˸�����˵��ȥ����ĸ������������һ�����Ӿ���������������ȥ�����ƺ����ڵ�������ᣬ�����������������ʱ�˵������ſ��˹����������ӽ��������˻�ȥ��
��������ij��ھ����ƶ����Եķص�ʱ��̥�������ˡ�
�����ҵ�һ�μ���������һ�����"�Ǹ��������˶�Ҫ���ˣ����繤���������������"
�������˼�״��Χ�ڳ��ԡ�
����������һ������Ļ��ͼ��ˣ�˵��"�ɲ��������ˣ�"
��������û����ĸ�Ļ������ưܵ�ƤЬ���ҵ����ų�̥��
�����������ҸϿ�ȥ�������ʦ������������̥���Ҿ�ȥ�ˣ�����ȥ�ġ�
������ʦ������Ħ�к��ҵ�������ʱ�����Ѿ��������������ڷɱ���Ħ���Ͽ������Ͷ̹��Ƕ������������ĺ����ϣ���ɫ�����������������ϡ��Ǹ�ʱ���������ر�ļ������Ҿ���������������ʵ���ͻ���������һ֧����������ũ���ֶӣ���ؾ��������ݳ�����̨��
������ʦ��һ����ָ�����˺����������̥������������ʦ���ð����ô���Ÿ�Ȧ���������ײ���峺�������������ڹ��������ϡ�������������˶���Ը�ſ�˵����ֻ�и��������ź��ţ������˲��ڷص���������ǣ����춼�ǡ�
������̧ͷ���죬̫�������½���������ճ���һ�����Ż��������������һ���㡣
����һֱ���������һ���ƶ����˻��˼ҡ�
���������������������������������æ�Ļ��˼ң�Ҳû˵����ĸ��һ��ؼҡ���֪�������弱æ�ؼҿɲ���Ϊ�˺����������£��Ҽǵ�����Ը���˵�������ǼҸ���ƶ���Ͳ����ݡ�
�������������ջ��ݰ�ĸ��ϴ�룬�����ڵȵ��˺���˵���Ļ��"�ܲ�������ô��"�������ʸ��ף�����ŵĴ��ġ�
����"�ⲻ����˵����ġ�"����˵��
������������Щ���Σ���˵��"�ǿ����Һ���ͷ�Ӹǵķ��ӣ�����á�ȥ����Ů���������Ǹ�����ǧ��Ǯ�ģ�"
����"����˵����ȫ������һ���ջ��ݡ�"����˵��
�������Ļ��û����Ӹе��˿ֻţ�����æ���ʵ���"�ǣ����Ժ����������ǻ���ס���ģ�" ���׳�Ĭ�ˡ������ش��������⡣������ͣס��ϴ�룬�����ͽ���������Ҳ�����ĸ��֮��Ϊʲô��Ū���������ҿ�ʼͬ����λ���ˡ�Ȼ�������ӵĽ������Ļ��������Ҿ��ȵģ���˵��"��Ը����������Ǯȥ����Ƿ��ӣ����������ݲ��ܲ��Ժ����ǻ���Ҳ�и�ס����"�Ҿ�������ǰ��С���������ˣ�������ʮ�����С�������ܻ�����ô��Ǯ����û�뵽�ġ�����ʱ����д���ģ�˵��ȥijij��ɷ�ijλ��Ԫ������ʱ�����Ԫ�������ж�ţ�ˣ�
����"��ȰȰ�����ɣ��ܲ������ҾͲ�֪���ˡ�"���׳�Ĭ��������˵��ȥȰ����Ļ���
����������Ц�ˣ����ƺ��õ���һ�����ϣ�����������ʱ�Dz�����ˡ�
�������������ˡ�����ĸ�������Dz��ǻ����ӵ����ӣ�ĸ���������۾����ң���ʵ���Dz�������СС��͵��һ������������⡣��˵���裬�ҳ������ٲ�����ǰ�Ǹ�Сƨ��������С����ĸ��˵������ԭ�������Լ��ĺ��ӵĿ�ز���ˣ������ǻ����������ĺ��ӡ�
�����������ϣ�����ȥ������ҡ�
�����ڶ��������Һ�������������ڴ��ϵȴ��Ż����ӵ�ߺ���������Ѿ�ϰ��������������Щ���꣬��֪����һ�ķ��϶�������飬���»����Ӳ���ߺ�ȣ����������ӡ�
����Ȼ���ҵĵ����Ƕ���ģ�����ȷ��ʱ���������˻�����������ߺ�������������������ҼҺ̳��ϵ��ң��ҿ������ѵ���Ъ�����Ǽ���ǰ����ɼ���¡���ɼ�����ҳ�����ʱ������ˣ��ü����˲��ܻ�����ס���Ҳ���������ΪʲôҪվ���������£�Ҳ����ɼ���Ĵ�׳�ܸ�����ȫ�С���������Ц�ţ������Ľ��ҵ����֣�����Ҳ����졣��������ס�����ݡ��ɾ͵������Ӱ����ӵݸ��ҵ�ʱ��ͻȻ����һ�����졣����Ϊ��Ҫ���ˣ�������ͷ�����ߣ�����û���������������ĵ�������ɼ���£��������Ǻ�����һ���µġ��ѵ������Ӻ���������ij����ϵô��
�����������Ǹ����罫����Ķ���ȫ����ɨ�������Ƶ���ը������ը�������ݣ�ֻ����һ���ջ��ݡ�����ľٶ���ȫ���˶��ܾ��ȣ���ȫ���˶��������˲�����Ϊ��û��˭�����������ӵġ�
������������ƽ���Ľ������һ�С�
�����Һ�ĸ���������ͻؼ�ʱ��������Ѿ�������Ҫ���ߵ�ש�飬�ҿ������Ӻ�����İ���ש�顣�Ҳ�֪���������ϸ�������ôȰ����ģ�����������ô�ش��ġ�������ʲôԭ���ʹ������������������춯�ص����飿����һֱ����ʱ��û�����ң�����һ���ԣ�һ�������ּ��ԡ�
�����Һ�ĸ�������Ӱ������ջ�����ʱ���ľ�崲�ϡ�������������ʱ��˺���ѷεĿ��ţ�����ɤ�źܴ֣�������һ��ɳ��������˱������Һ��
������������������ש��ʱ���ﻨ����û��û��û�ȣ���ƾ��ͷ��ôιҲ���ԡ���������ͷɢ�������ڴ�������ͷ�ӣ�"��Ϊʲô�����ģ��������һ��ģ��뺦��������������"
������ͷ�����˻����ӵĻ��̲�ס�����ݺ"���������Һ���ǵģ�����ô�Ầ�㣿����Ҫ����ʲô�취�����϶�������Ͱ��Ĺ����Ӱɣ�"
��������������ש����������꣬���ź��Ƶ����������������������ǼҵĻƶ�û���ü������Ͳ����š�����������һ�����ͽ������Ͳ���ƶ����¶�ȴ�����������ƶ���ʼ��ø����ѿ��
�������Ǹ��־õ��꼾����ͷ�������ֳ����������Ե��س�ҽԺ��飬�������з硣��ͷ�ŷ��ֻ����Ӳ�Ը������ԭ�����������ˡ�
����������ԭ��ֻ��������������֪���Լ�������ȴ�������ˡ�����������һ���Ӽ���ȥ���������ӣ�˵����������ô������Ǯ�α���ô�벻������Ҫ�úõĻ��š���ͷ�Ҹ���������ͷ��һ�����������Ϳ����µ���·�ˡ�
������������������һ��������ĸ����ȥ�������Ժ�ÿ���糿����Ҳ�����������ӵ�ߺ�����������Ѿ�ϰ��������ߺ����������������������������ӡ�ÿ���糿�Ҷ�ʱ������ʱ���ҾͿ�ʼ�ֻţ����ꡣ
������һ���Ҿ�Ȼ�ڰ�ҹ�����ˣ���ʹ�Һܰ��ա����DZ�"����"�Ŀ��������ѵģ��ѵ��ҵ���������������ϣ�������ڿ�����Զ�������ϵ��������ǣ�ʲô�����ǣ�����������ʲôţ�������ҳ������⿴ȥ�������������������ҵĿ�����ǰ����ɼ�����Ҽ�æ��ȥ��ֹ�����ľٶ����ɸ���ִ��Ҫ��������˵���������������ɼ���µ��µģ������������������˵������ɼ�������˻����������ӵIJ�Ҳ��á���ɼ�����ɾ��ˣ���ÿ��ˣ�
����������һҹ��ʱ�佫��ɼ��������
������ɼ����֤���ҵij������Ҽ�֤����ɼ����������
��������"������"��Ȼ��Ч����������ij�糿��ʼ���Ź���ȫ���߶����������ˡ��������������Ǵ��صĴ�������ֻ�Ǹ��Ӽ����ˡ�����������������š������ȱ�ԭ�������ˣ����ڵ��Ϻ�����̧������
���������ӵļ�ֶ������Ǻ���Ч�ġ�������ɫ��ʼ����Ѫɫ���������ߺܶ�·�ˣ�һ���ܳ������뷹��˭�����������ȥ���뷹�ԣ����Ѿ�����������Ҳ��������������˵��һ�ж��鹦����������ɼ���������Ǹ����������Ҳ����Ÿ��Ļ����������Ż��������ٻ��ܻ����꣬�����������������������ӡ�
�������ش����������˰���£�����ʮ��������Ĵ����Ȼ��ֹ�������ڴ��������������ı�������ƽ���ʷű��ڣ��ǿ϶��������ˡ�
������������˵�������dzԶ���ҩ�ж������ģ�Ҳ������˵�������DZ��Լ�����ͷ��������ҩ�����ģ�������û���չ˻����ӡ���ô�����Ҳ��������������һ���Ǻ���ʵ�ģ������ڻ����Ӽ�����ȥʱ��ͷ�Ӻ�Ȼ�����˻����ӻ���������֪ȥ����ͷ���ʻ����ӵ�ʱ�������������۾�ȴ˵����������
�����ڰ����껨���ӵĺ��º���ͷ�������������ֶ���ȥ���سǡ�
��������飺
��������ԭ�������������������ˣ�80������С���Сϲ����ѧ�����ڳ���������ȴ�Ӱ�������ѧ����Ʒɢ���ڡ������������人�������ȡ�
����Q Q��332347624
����E-mail:tns2000@163.com
�����绰��13071223133
������ַ���人����㹫Ԣ¥B��2405
�������ҹ���¹��ɭɭ�ġ�
���������ڼ��ж��������˴���ͷ��ûϴ�������������ƶ�����Ѹ������ȥ���������������ݵ���ʱ�һ������������һ���μ�һȺ������ɫ��װ������ս����Ҳ�����������ģ���Щ����Ҳ���Ѳ����Ǹ�խխ��������Ȼ��ͽ������ĺ�����������ϣ�Ҳ�����Ǵ������ӵ�����������ӵ����õ��˿����������ļᶨ��׳�ҵ���ȥ���������������ˣ��Ǹ��״�����ⳡ"ս��"���ҷ·�ǵ���һ��Ҳ�����������Σ���������һ�ε������������ġ�
�����ҹ������ݵ���ʱ������˵��"��ţǣ����Ժ��"
���������Ҵ����ڿ��ȥţ����ǣţ����û�뵽Ҫ���·�����Ϊ�һ���Ŭ�������Ź��µĽ�֡�ţ�������Ӻܶ࣬������Ѹ�ٵ����˺ܶ��ɫ��С��������ţ���͵ij�����ڵ��ϵ�ţ��������ţ��ǣ�������Ӿ�������һ����ӵ�Ÿ��˳�����
�������ʱ��Ĵ����ǰ����ġ����ڵ��˼��Ѿ���ҵ��سǣ���Ժ�ӵ���ľ���Ӳݶ�����һ�𡣰�ɭɭ���¹�����������һ�㱡������������һ��������ȥ�ı�����ȥ�����̡����̴��������ӳ�������
����ǣ��ţ�һ��ݼ���˯�������ڴ��ϰ����ĵȴ���һ��ߺ�ȣ�"�����ӣ�������ͷ֮�����㣬�����Ľз����DZ��ӣ�������"ߺ������ɳ�ƣ�������һ�㣬������Զ����ʹ�ڼ�ʮ���������ﶼ����Լ���������dz����С�̷������������ġ���ʱ���Һ�С����Ը������ߴ�����������ũ�˳������ˣ���Ϊ����ڴ�����걾ʽ��ũ����˵�����Ǽ������ģ����������ǵ�ߺ�����������ɣ�¶����Ȼ��Ұ�ԡ�
��������������Ҳ��Ҫ�ֵصģ��������͵ü���ʱ�����������������������������������糿Ҫ�ȵ��ˡ����ڵ������¿�����һ�����Ҽ�����ߺ��������Ȼ���ٷɱ������ӣ�����Ǯ�����ӵ������ó��Ⱥ��������ӡ�ÿ���Ҷ��dz�Ĭ�Ŀ������ƶ���˫�֣���������ҪЦ��һ�������ƽ���"������"���ҵij�Ĭ�Dz�֪���������ƺ��������ĸ������ҵ�үү���DZ����ˣ������е����Ĩ�ǵĹ�ϵ��������һ���㲻֪���������ƺ�������Ҳ���Ŵ��˽��������ӡ��Ҳ��������ԭ����һ�������������ϳ��������ӣ��������Ǻ�ϲ��Ц�����ܲ���ȥ��������������Ƭ��������š���ƫƫ���������������Ǽ�ϲ���ģ��Ҳ�֪��ÿ���峿�������ڵȴ�������ж������ڵȴ�����֮����С�����糿��һ���羰��
��������ʮ���ʱ�������Ѿ���ʮ�����꣬��Ȼ����һ�ֺ����ӣ�����ҲӲ�ʣ����ŵ�����·������ꡣ�����֣���Ҳ�֣��Ų�ȴ�ƶ��Ŀ죬�������̳���ʱ���������������صĺ�������
�����ٴ����ڴ��ϣ�������˯�IJ����ȣ����Ժ����������ְ�ɭɭ�����������̵������Ҽ����ر�����������������һ��ߺ���ܾ��絽�������������᷿��ĸ������������������������ʹ����������ʱ����Һ�������������һ��ʲô���IJ�����ĥ����ҹ�����¡�����ȥ��ο����ȴ��Щ�ķ������뵽�����������ջ�ļ���һ���˳е�����Ͷ�����
�����Ժ����ҼDz�����ߺ��������ǰ��������ʲô�����뵽��ʲô��������������ϲ�����������Ҵ�������һƬʱ�Ҹо���ߺ����һֱ���Ҷ��ϻ��죬��������ʱ����������������е����Ҷ������������ץ�˼��·��ͱ������ݣ������������������Ŷ��ص������һ��ɻ�����������ʶ���ʵ�ʱ��������Ҽ���ǰ�ະ�˼�ɤ�ӣ���Ϊ���ҳ���ʱ���պ�վ���ҼҺ̳����롣��Ȼ����˵��
����"�����ӣ�������ô��һЩ��"
������������û�лش�������Ĭ�İ����Ǯ�ݸ��������������İ�Ǯ�������ӿڴ����װǮ��ʱ�����Ǻ��������ܿڴ������Ǻ�������Ҽ�����Ը�Ŀ�������֫�ϵ��⣬��������������������֫�ķʺ������������ʱ��Ҫ�������ӡ�Ȼ��������Ҫ�����µģ����ƺ��ܴ��ġ�
����"����զ����ô�ࣿ"�����ʣ�����û�ش�ĩ�����Լ��ش�" ���Ǽҽ����ջƶ����������˶̹��ˡ�"��֪�����������ǹ����ʵģ�ÿ�����ʱ�����������ҿ���˵��������û�������ó�һ�Ρ�����Щ���⡣
��������������Ǯ�������ӣ�Ȼ���ٺ����������ŵ����ߡ�����Ҳ�������ڻ��ݣ����ƺ���ϲ�������ı�Ӱ�ģ�ȷ��˵��ϲ����������������·����ʱ���ұ�������Ǵ��������˵�ǿ�ߡ��ҳ�����������������Ľ��������������Dz���������ү���ƹܣ�
���������������������г�������ĸ��ס��Լ��̹�����ȥ���̹�Ҳ������ͬ��ĸ�Ů�����Ǽ��е��Ǹ����˻ƶ����е��ǻ������ո���������Լ�����Ŀ���ʱ������顣�̹���Ҳ��һ������ڵ���æ���û���緹���������ǰ���͵ij�ʳ�����һ����˵��̫���ڿ�����û�Ǯ�ȵȡ���������Ȱ˵�����Dz�����һ�ѻƶ����ϳ����������Եļ���ϸ,�����DZ�����������������ϡ�
������������һ�Ҫ�ؼ�ϴ�·�����ú¯����
�����ҵ��Ƶ����ɱ����﹣�ϣ��﹡���Ǻ�խ������·�涼��������ݣ�ֻ���м���һ���͵�������һ������·¶����ɫ����������ͯ��Ļ����˵�������Ѿ�ϰ��������Ƶĵ����ɱ���������"����"�ϡ����ǵij��о���ÿ�����طɱ���������"����"�ϣ�����ѧ����ææ�ؼҳԷ������˷��ּ���ææ��ȥѧУ��������Ҳ�����⡣����·�ϵ�ʱ�����Ժ����ܻ�ij�³Ѹ������һ�仰��"���ϱ�û��·�ģ��ߵ��˶���Ҳ�����·��"
���������Ķӵ�ת�䴦���˸���ɲ�����������Աߵ�������������ȳ��ŵ�����ҵ��ȶ�ֻ�ÿ����³�������һ�ߣ��������������������ͨ�������忪�������ļ������������ܻ����ϸ�Ŀ�������С�ĵ��ƹ�һ���������������ٿ�������һ����������ӣ������һ���������Ƕ������������ˡ�
��������ļ����ܺã���������ũæ��ʱ����������ת�����﹡�ϡ�������Ѱ����Ҫ���˵����ˡ�
����������Ҳ�������ˣ���������ʲô�������գ�ר����С����Ķ����������ʱ������һ��С�������ҷ��������С�����������ڵ��ϻ�����������������塣�����ǰ�������Ϸ���������ܻ���ִ�������ࡣ�������ǻ��������ľ����³��֣��Ի������ǽ��ŵ����档��ʱ����������ͯ������������Ŷ���ʽ�Ĵ����г���������ÿ��ÿ���ĺ̳�ǰ�����Ķ������г��Ϲ����˸�ʽ������������˵�ĸ�ʽ���������ǵ�ָ�������ɫ��ͬ������˵����������죬�е���ƻ�����е���Ѽ�ӡ��е���ëë�桭��������Щ���dz���������֡���ʱ����һ����������Ǹ��������ɵ��ˣ������ǻ��кܶ��������С����ע������Ȼ�����Ƕ��ֻ���۲��ſ����Ӵ���ͷ������ͷ���������"����"Ϊ�����γ�һ���Ӵ��ϵͳ����������Χ����������ҲΧ�������������ƶ��š�
��������Ķ������г��ͻ����ӵĵ���һ���Ǵ���ķ羰��
�����Ҽǵ������������һ������ġ�������������Ҫ��ĸ�������ĸ�ײż�����Ը��������ëǮ���ҡ��õ�Ǯ��ʱ�������Ѿ����˺�Զ��һȺС����ӵ�����ϵ������壬��ϸ�ĵ���ѡһֻ���Ŵ��ǵ�"����"������ͷ�����Ӻܿɰ���Ȼ����û�кúõ���ϧ����"����"��С����ǵ���������һȦ���Ҿͽ��������������һ����Բ����������ѧ����������Ӱ������"����"�����ӣ��������ܰ�������������Dz�������ô�䶼�䲻���������°�����Ū��ԽŪԽ������ȥ��ĸ�ף�ĸ��һ���ҰѸ������������˾������Ǹ��ܼ��ӡ�����ĸ�װ�������"����"��ĸ��˵�Ҳ�����ȥ�����塣�����Ҿ�ȥ�����壬������˵����ȥ�������Dz���ά�ģ�������������Ǯ��Ҫ��Ȼ����Ǯ�ˡ���˵������ֶ������Ӧ�ð�æ�ġ�����˵ֶ��Ҳ�����������Һ�����˵����ʱ��������������ͷ�����ջ��������棬�����������ȳ�ˣ�����������Ħ�����̶������졣��ͷ�����̲�ͣ�Ŀ��ԣ������ջ���ӽ���ڲ����������ơ������ϱ���ͷ�Ƣ���ˣ�վ�����ݳ��ջ��ݳ���ɤ�Ӻ���"����Ѭ����ѽ�����̻�Ѭ������"�Ҽ����"����"������ת�����ؼң���������һ��µ���������ݣ�Ц�Ŷ���˵��"��ʱ�䳣���氡��"�һ�ͷ����������Ц��ȷ�ÿ����ֲ��ù��յ�����ҪȢ�������š�
�����ұ��Լ�����һ�����Ҳ�֪���Լ���ô�Ͱ�����˵�ɹ��յ��ˡ��ѵ���������������������������ǰ�������е������������Ϊһֻ�������ƻ��ˣ��Ǹ�ʱ������ѧ����һ����ȵ��ˣ����ҷ����������ˡ�Ҳ���������Ļ����������������뵱��������������һ�Ų��ƣ����ұϾ����Ǹ�С���ӣ���û�����������ߵ�������Ҳ�Զ�������ɼҵ���˶��Ա����������һ�Ž�����Ǽһ�����ҵĺ���֮��һ���ᱻ�����������һ����������е����塣�ɵ��һ�ͷ�����������Ѿ������ˣ�Ҳ��������û�����ҵĺ����ٶ���Ҳ����������ʱ���������������ƨ�ɽ����ݡ�
�����������������
�������ȷ�Ǻ��ˣ����ǿ�ʼ�����ˡ��ҵ�������ʼģ�����ѹ��ҵĺ����ٶ�û���˷�����������һ�������������˵����硣���DZ����Լ���Ӧ��ѡ��һ��������ʱ�������ʱ��Ĵ���æ��һ�죬Ů������ƣ�����������˵���������������������̶��ں�Ժ����ţ�Բݵ��ų�ʳ����ţ�Ƕ������˵ģ������˲���ҪŮ��ʱ��ţ��������Ψһ�Ļ�顣
����������һ�վ����˶��ԣ��Ҽ�����Ը��ڣ���Ϊ���ƻ����ҵ��ж�����ϣ�����������̳��������ҿ������ϵ�������Ƭ��Ȼ������û�У���������ĵ������ˣ�������Ҫ�������Ż������
��������һ�λ���������������Ц�����ſɰ�������ӳ���˺�ɫ�������
�������뿪��˶�ؼ�ʱ��ֻ�������ŵķ��������������־�ļ�С�ԭ����һֱվ����˶��Ա��⼸ֻ���ŵIJ��һ�����������ʹ���������˳����������"��辫���ģ��㺦��ȥ���ģ�"���������ɣ����������������������Ѹ����ʧ�ںڰ��
���������Ǹ��˾������������������������س�����һ�˵������Ҫ�뿪������ġ�һ��������Ⱦ�ʱ���������˵��
�������뵱�����ٴ���������"����"�����̳�ʱ�һ����������С������м�������мһ�˵ı��顣Ȼ������û���������ˣ���Ҳ���ٿ������������﹡��ת���ˡ����ƺ�������ʼ����"��ũ��"�ƻ��ˡ��ҵļƻ���һ����ա�
�������ǼҵĻƶ�һ���������졣��Ϊ�����������ƶ�Ҳ������������Ȼ���ڵ��Һ��������壬���һ��ǻ��������������������������˻ƶ�������һ��Ϳ��Խ�����ɻ����չ��ǻ��롣��ʵ����ǣ�Ż�ţ�������ƹ��Ű峵�Ѷ���һ�峵һ�峵�����ˡ�
�����ڶ������ǻ���������������������������Լ����������ġ�
����ĸ���������õ�ʱ������ͽ������Ǽҵ��š������ĸ����⣬���һ�����϶���Ц��˵��"�����������ˣ������ѣ�"�Ҹ����Ǻ����������ȾƵģ����ϾͰ�����ꡣ��������ȥǰ��ȡ�þ������ҿ���һ�����壬���廹��һ����Զ��Ц�����ӡ������˸��Ļ�ȥǰ�ݣ�����û�þơ��ҲŲ�������þƣ�ĸ�����ϰ���ȡ�����ƣ������ջ��ݺ�����ƫ�Dz�Ӧ��ĸ���Լ���ȡ��,�����Ǹ������ò��졣ĸ��������������Ҹ��ᷳ����֪�����������һ�������飬���������������ŵġ�
�����ҽ����ݵĵ������Ҿ����ںڰ�������ջ�����ĸ������塣�ջ��ݵĵ���Щ���������ϻ����˻ҳ���֩��������ֻ�����ĺ�è������ú¯��������Ŀ������ϵIJˣ�Сè���ڵ��Ϸ����������ȥ����ͻȻ��Ц����Ϊ��ʱ����ı������ֻ�Ϻ�èһ��������רע�Ŀ��ű�����ľơ�
�����������ں���һ���Ʋ�����˵���˴��е�Ŀ�ģ����Ǿ�����˼���˲����������ִ���һ�ֵ��ĵ�������"�ϳ�����Ҫ�ڳ��ィ���ӡ�"
����"���Ǻ����ۣ�"�����žƱ�Ц�ˣ�����Ц������������˿��ǵ�̫���ˡ�
���������ֳ�Ĭ�ˣ������Ͳ�ס�����ˣ�"��ɶ�����˵�ɡ�"
����"��Ҫ������ݣ�"
����"��������ͬ��ô��"����һʱ���뵽��������⡣��Ҳ��������ͬ�����ĵ����⡣
����"��ͬ��Ҳ��ͬ�⣡"��������������˾��ġ�
����"���������а���ô��һ��ȥ���"
����"������һ���ջ��ݸ����ϰɡ�"
�������������������������˼��һ��ͷ����һ���ƣ�����һ���ƣ�˵"�ã�ɶʱ��������һ�����У�"
����"����Ͳ������ҿ��������������˻ƶ�����ϱ��Ҳ����æ�"����˵��վ����Ҫ�ߣ���������������˵�ٺȼ���������ִ��Ҫ�ߣ�����Щ���ˣ��Ųȵ���Сè��צ�ӣ�è������˺���ѷεļ�С��Ϻ�è�ø�����������ŵĵ���Ѹ�͵���������������ϴ���ĸ��ӦҲ�죬�����е�Ĩ���ӵ���è���ϣ���������һ������ôЩ�꣬���Ѿ�ϰ����������è����Ϸ��
�����ڶ��������Ȼ�����������������������ǼҵĻƶ��ء����忪����Щ�������ײ����ƶ�����̫�š�̫�������ո�ļ��ھͻ����������Ұ��������ո�ʱ��©�Ļƶ������˲�ע��ᳶ��һЩ�ƶ���
�������彫�����������յ��ϣ��������ڼ�ʻ���ϵ����Ǹ���ƶ���һ��һ��ı��ϳ���
������Ȼ������ʱ�ڣ�̫�����Ǻܶ�����������������ͣ�ĻӶ�������������ɳɳ�����졣һ˿��Ҳû�У���ˮһ���ӾͰ�Χ���������̵��۾����ۡ���ʹ��Ů�̹����������������½�������ϵĺ�ˮ�������ɱ�����Ӿͱ�¶�������¡�
���������ٽ������������������һ���ܺÿ��ĺ�ɫ���£����·��������������ĺ�ϸ����������Ƥ���ͺ�ɫ���������γ������ĶԱȡ��ҵ��������ᵹ�����
����������Թ���������䣬˵�������æ���������Լҵ����ݡ��������������壬�������һ��ˮ��������ƶ�����ô�ȵ��춮�õ��������ׯ���˻���Լ����ľ�������Щ�����������촩��һ��������ϲ������ţ�п㣬������ʱ��ƨ�ɾ���ϸߣ���һ���Ӳ��ʯͷ��Ȼ�������ƺ�ûע����Щ��Ҳ�ѹ֣�ũæ��ʱ����˭��������Щ������ûע�һ�Ե�������������͵͵�Ŀ�����
���������Ǹ������ˣ���������Ҳ����ĺܿ졣
�������ǻ�����������һȺ�ȳ�����Ŀ�����"Ұ��"��
���������Ͼ��Ǹ����֣�ֻ����һ���վ�����������ͳ��ÿ��������ߺ����Һ��ź���û�������½��������Ȼ���Ľ����������ò������ģ�������Ҳ���ܿ�����Բ������ӣ���Ϊ������ũ�帾Ů���������֡�
���������ָ���һ�����Ұ�ˮ���ù�ȥ��ˮ��ũ��ũæʱΨһ�ܻ����������Һ������������ˮ������һ��һ��Ŀ����������Ҳŷ����������������������ͽ��������������ĺ��������������Ӿ�������һ����������������"����"�ε�����Щ�Ļ����ҡ�
���������·�������ʵ����ˮ���ܻӷ������ı���ʪ��һƬ����̧ͷ����ʱ������Ҳ��һ������������ϡ�
����"Ī����Ҫ�����˰ɣ�"������ʶ�ĺ���һ�䡣���������ҵĺ������쿴�����ƣ�˵��ʱ�����¡������Ÿ��Ļ�����Ϊ�����Ǹ��걾ʽ��ũ���������Ƹ������а��յġ�
�������Ǵ�����ﻹ������һ��ʯͷ����Ҽӿ��˽��ȡ�
���������ʱ���������������������������Щ���ⲻȥ��˵����IJ���˾Ͳ��ͷ����ˡ�������˵�Ҽ���Ҫ��������ˣ���һ���˾Ͷ�һ��������˵�žͻ�����������������û��˵ʲô������֪���������������ø���Ȱ�����Ӳ�Ҫ������ݡ�
�����������������ȷ�˵ĺܿ죬����Ҫ��ʮ���������˵Ļƶ��������ˡ����忪������������խ�﹡�����ص����ţ��ƶ��ں����϶ѵ��ϸߣ������ж��ķ��ӡ�
��������Ҫһ���Ϳ���ȫ�����꣬ʱ����������ĵ㡣˭��û�뵽����ô����չ�����Ҷ��ڵ���ȴ������������������ȥ���ϰ��컹û�����������ӽ����ֵ�������������֦�£��������û���������ˬ������ȴ���磬���һ���Ũ�Ҵ̱ǵ�ũҩζ�����Ż����ӵĹ⾰�Ҹ�����ȥˮ��������ûЦҲû��ˮ������Щ�����ҵ�һ�ζԻ�������ô�ÿ���û���顣
����������ͣ���ò�ñ���ŷ磬�����˸�����˵��ȥ����ĸ������������һ�����Ӿ���������������ȥ�����ƺ����ڵ�������ᣬ�����������������ʱ�˵������ſ��˹����������ӽ��������˻�ȥ��
��������ij��ھ����ƶ����Եķص�ʱ��̥�������ˡ�
�����ҵ�һ�μ���������һ�����"�Ǹ��������˶�Ҫ���ˣ����繤���������������"
�������˼�״��Χ�ڳ��ԡ�
����������һ������Ļ��ͼ��ˣ�˵��"�ɲ��������ˣ�"
��������û����ĸ�Ļ������ưܵ�ƤЬ���ҵ����ų�̥��
�����������ҸϿ�ȥ�������ʦ������������̥���Ҿ�ȥ�ˣ�����ȥ�ġ�
������ʦ������Ħ�к��ҵ�������ʱ�����Ѿ��������������ڷɱ���Ħ���Ͽ������Ͷ̹��Ƕ������������ĺ����ϣ���ɫ�����������������ϡ��Ǹ�ʱ���������ر�ļ������Ҿ���������������ʵ���ͻ���������һ֧����������ũ���ֶӣ���ؾ��������ݳ�����̨��
������ʦ��һ����ָ�����˺����������̥������������ʦ���ð����ô���Ÿ�Ȧ���������ײ���峺�������������ڹ��������ϡ�������������˶���Ը�ſ�˵����ֻ�и��������ź��ţ������˲��ڷص���������ǣ����춼�ǡ�
������̧ͷ���죬̫�������½���������ճ���һ�����Ż��������������һ���㡣
����һֱ���������һ���ƶ����˻��˼ҡ�
���������������������������������æ�Ļ��˼ң�Ҳû˵����ĸ��һ��ؼҡ���֪�������弱æ�ؼҿɲ���Ϊ�˺����������£��Ҽǵ�����Ը���˵�������ǼҸ���ƶ���Ͳ����ݡ�
�������������ջ��ݰ�ĸ��ϴ�룬�����ڵȵ��˺���˵���Ļ��"�ܲ�������ô��"�������ʸ��ף�����ŵĴ��ġ�
����"�ⲻ����˵����ġ�"����˵��
������������Щ���Σ���˵��"�ǿ����Һ���ͷ�Ӹǵķ��ӣ�����á�ȥ����Ů���������Ǹ�����ǧ��Ǯ�ģ�"
����"����˵����ȫ������һ���ջ��ݡ�"����˵��
�������Ļ��û����Ӹе��˿ֻţ�����æ���ʵ���"�ǣ����Ժ����������ǻ���ס���ģ�" ���׳�Ĭ�ˡ������ش��������⡣������ͣס��ϴ�룬�����ͽ���������Ҳ�����ĸ��֮��Ϊʲô��Ū���������ҿ�ʼͬ����λ���ˡ�Ȼ�������ӵĽ������Ļ��������Ҿ��ȵģ���˵��"��Ը����������Ǯȥ����Ƿ��ӣ����������ݲ��ܲ��Ժ����ǻ���Ҳ�и�ס����"�Ҿ�������ǰ��С���������ˣ�������ʮ�����С�������ܻ�����ô��Ǯ����û�뵽�ġ�����ʱ����д���ģ�˵��ȥijij��ɷ�ijλ��Ԫ������ʱ�����Ԫ�������ж�ţ�ˣ�
����"��ȰȰ�����ɣ��ܲ������ҾͲ�֪���ˡ�"���׳�Ĭ��������˵��ȥȰ����Ļ���
����������Ц�ˣ����ƺ��õ���һ�����ϣ�����������ʱ�Dz�����ˡ�
�������������ˡ�����ĸ�������Dz��ǻ����ӵ����ӣ�ĸ���������۾����ң���ʵ���Dz�������СС��͵��һ������������⡣��˵���裬�ҳ������ٲ�����ǰ�Ǹ�Сƨ��������С����ĸ��˵������ԭ�������Լ��ĺ��ӵĿ�ز���ˣ������ǻ����������ĺ��ӡ�
�����������ϣ�����ȥ������ҡ�
�����ڶ��������Һ�������������ڴ��ϵȴ��Ż����ӵ�ߺ���������Ѿ�ϰ��������������Щ���꣬��֪����һ�ķ��϶�������飬���»����Ӳ���ߺ�ȣ����������ӡ�
����Ȼ���ҵĵ����Ƕ���ģ�����ȷ��ʱ���������˻�����������ߺ�������������������ҼҺ̳��ϵ��ң��ҿ������ѵ���Ъ�����Ǽ���ǰ����ɼ���¡���ɼ�����ҳ�����ʱ������ˣ��ü����˲��ܻ�����ס���Ҳ���������ΪʲôҪվ���������£�Ҳ����ɼ���Ĵ�׳�ܸ�����ȫ�С���������Ц�ţ������Ľ��ҵ����֣�����Ҳ����졣��������ס�����ݡ��ɾ͵������Ӱ����ӵݸ��ҵ�ʱ��ͻȻ����һ�����졣����Ϊ��Ҫ���ˣ�������ͷ�����ߣ�����û���������������ĵ�������ɼ���£��������Ǻ�����һ���µġ��ѵ������Ӻ���������ij����ϵô��
�����������Ǹ����罫����Ķ���ȫ����ɨ�������Ƶ���ը������ը�������ݣ�ֻ����һ���ջ��ݡ�����ľٶ���ȫ���˶��ܾ��ȣ���ȫ���˶��������˲�����Ϊ��û��˭�����������ӵġ�
������������ƽ���Ľ������һ�С�
�����Һ�ĸ���������ͻؼ�ʱ��������Ѿ�������Ҫ���ߵ�ש�飬�ҿ������Ӻ�����İ���ש�顣�Ҳ�֪���������ϸ�������ôȰ����ģ�����������ô�ش��ġ�������ʲôԭ���ʹ������������������춯�ص����飿����һֱ����ʱ��û�����ң�����һ���ԣ�һ�������ּ��ԡ�
�����Һ�ĸ�������Ӱ������ջ�����ʱ���ľ�崲�ϡ�������������ʱ��˺���ѷεĿ��ţ�����ɤ�źܴ֣�������һ��ɳ��������˱������Һ��
������������������ש��ʱ���ﻨ����û��û��û�ȣ���ƾ��ͷ��ôιҲ���ԡ���������ͷɢ�������ڴ�������ͷ�ӣ�"��Ϊʲô�����ģ��������һ��ģ��뺦��������������"
������ͷ�����˻����ӵĻ��̲�ס�����ݺ"���������Һ���ǵģ�����ô�Ầ�㣿����Ҫ����ʲô�취�����϶�������Ͱ��Ĺ����Ӱɣ�"
��������������ש����������꣬���ź��Ƶ����������������������ǼҵĻƶ�û���ü������Ͳ����š�����������һ�����ͽ������Ͳ���ƶ����¶�ȴ�����������ƶ���ʼ��ø����ѿ��
�������Ǹ��־õ��꼾����ͷ�������ֳ����������Ե��س�ҽԺ��飬�������з硣��ͷ�ŷ��ֻ����Ӳ�Ը������ԭ�����������ˡ�
����������ԭ��ֻ��������������֪���Լ�������ȴ�������ˡ�����������һ���Ӽ���ȥ���������ӣ�˵����������ô������Ǯ�α���ô�벻������Ҫ�úõĻ��š���ͷ�Ҹ���������ͷ��һ�����������Ϳ����µ���·�ˡ�
������������������һ��������ĸ����ȥ�������Ժ�ÿ���糿����Ҳ�����������ӵ�ߺ�����������Ѿ�ϰ��������ߺ����������������������������ӡ�ÿ���糿�Ҷ�ʱ������ʱ���ҾͿ�ʼ�ֻţ����ꡣ
������һ���Ҿ�Ȼ�ڰ�ҹ�����ˣ���ʹ�Һܰ��ա����DZ�"����"�Ŀ��������ѵģ��ѵ��ҵ���������������ϣ�������ڿ�����Զ�������ϵ��������ǣ�ʲô�����ǣ�����������ʲôţ�������ҳ������⿴ȥ�������������������ҵĿ�����ǰ����ɼ�����Ҽ�æ��ȥ��ֹ�����ľٶ����ɸ���ִ��Ҫ��������˵���������������ɼ���µ��µģ������������������˵������ɼ�������˻����������ӵIJ�Ҳ��á���ɼ�����ɾ��ˣ���ÿ��ˣ�
����������һҹ��ʱ�佫��ɼ��������
������ɼ����֤���ҵij������Ҽ�֤����ɼ����������
��������"������"��Ȼ��Ч����������ij�糿��ʼ���Ź���ȫ���߶����������ˡ��������������Ǵ��صĴ�������ֻ�Ǹ��Ӽ����ˡ�����������������š������ȱ�ԭ�������ˣ����ڵ��Ϻ�����̧������
���������ӵļ�ֶ������Ǻ���Ч�ġ�������ɫ��ʼ����Ѫɫ���������ߺܶ�·�ˣ�һ���ܳ������뷹��˭�����������ȥ���뷹�ԣ����Ѿ�����������Ҳ��������������˵��һ�ж��鹦����������ɼ���������Ǹ����������Ҳ����Ÿ��Ļ����������Ż��������ٻ��ܻ����꣬�����������������������ӡ�
�������ش����������˰���£�����ʮ��������Ĵ����Ȼ��ֹ�������ڴ��������������ı�������ƽ���ʷű��ڣ��ǿ϶��������ˡ�
������������˵�������dzԶ���ҩ�ж������ģ�Ҳ������˵�������DZ��Լ�����ͷ��������ҩ�����ģ�������û���չ˻����ӡ���ô�����Ҳ��������������һ���Ǻ���ʵ�ģ������ڻ����Ӽ�����ȥʱ��ͷ�Ӻ�Ȼ�����˻����ӻ���������֪ȥ����ͷ���ʻ����ӵ�ʱ�������������۾�ȴ˵����������
�����ڰ����껨���ӵĺ��º���ͷ�������������ֶ���ȥ���سǡ�
��������飺
��������ԭ�������������������ˣ�80������С���Сϲ����ѧ�����ڳ���������ȴ�Ӱ�������ѧ����Ʒɢ���ڡ������������人�������ȡ�
����Q Q��332347624
����E-mail:tns2000@163.com
�����绰��13071223133
������ַ���人����㹫Ԣ¥B��2405
(������Դ�������� �༭���﷽��)
�ؼ��ʣ�
������ţ�
��������
����Ҫ��
�����Ƽ�
������������ˮ���乩ů ���������������ů
�����ձ�Ѷ(��������ͨѶԱ����һ��쿺�������)˵�����й�ů�����˵�һӡ����뵽��ú���������ſƼ��ķ�չ�������õ���...[��ϸ]
��������Ȩ���������
�� ������ӭ����ý�塢�����硢Ӱ�ӹ�˾�Ȼ����뱾�����г��ڵ����ݺ�������ϵ��ʽ��027-88567716
�� �ڱ���ת������ý������Ϊ�����������Ϣ�������������������۵㡣�������ת�صĸ���漰���İ�Ȩ������Ȩ�����⣬�뾡���뱾����ϵ�����������չ�����ط��ɷ��澡�����ƴ�������ϵ��ʽ��027-88567711
�� ����ԭ��������Ϣ������ȷ�����Եı�ʶ��������������������"������"��Դ������ת�ط����Ǿ�����ԭ����������Ϣ����Ϊ�����������䷨�����ε�Ȩ����
�� �ڱ���BBS�Ϸ������ۣ�����������������Ӧ�����ԡ�������������ط��ɷ��档
�� ������ӭ����ý�塢�����硢Ӱ�ӹ�˾�Ȼ����뱾�����г��ڵ����ݺ�������ϵ��ʽ��027-88567716
�� �ڱ���ת������ý������Ϊ�����������Ϣ�������������������۵㡣�������ת�صĸ���漰���İ�Ȩ������Ȩ�����⣬�뾡���뱾����ϵ�����������չ�����ط��ɷ��澡�����ƴ�������ϵ��ʽ��027-88567711
�� ����ԭ��������Ϣ������ȷ�����Եı�ʶ��������������������"������"��Դ������ת�ط����Ǿ�����ԭ����������Ϣ����Ϊ�����������䷨�����ε�Ȩ����
�� �ڱ���BBS�Ϸ������ۣ�����������������Ӧ�����ԡ�������������ط��ɷ��档
对不起,您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已被删除!
10 秒之后将带您回到荆楚网首页
要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