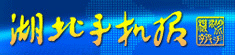�˾�
����ʱ��: 2009-11-23 17:22 ��Դ: ������ ������ӱ�
�����ƶ������ƶ���Ҳ���β���վ��������������������������������ߡ��ɿ���Ժͷ����ľ������ճ���ˣ����������β����϶��ƶ����ڼң��ƶ����ܰ�ҹ�����ܰ�˯���˯��
��������Ӧ������ȡ���ȣ��ƶ�������Ұ��ȥ�ǣ�
������֪���ƶ�������ǹ��һ˵��ɽ��Ұ�����������ز����ˣ������ǹص���˿�Ϸ졣��·��Ժ��Ҫ����ʮ��ʯ���ݶ��������������������ž���ˮ����˳�����ο����ӣ����˿��վơ����ú��죬���ֱ������һĨ��������ǹ��ĸ���һ�𣬱��𣬻ƶ��������վƴ�ǹ�ǣ�����Ժͷ�Ǻ�����ľ���е�����Ӧ��������������������ţ��ΰ��ӱ߿������¿��ӿ����������Կ�һ˦����һ��̵���Աߣ���Թ˵��Ӳ�ǣ��Ͷ�����զ��������ѳ��ͺ��������˯û˯�ѣ������ݻ��ˡ��β�����������һ������̫��ʺ��������Ц�ã�˵�˯��ɶ˯ͷ����������˯���٣��ߣ���ǹȥ���Ͻ�Ǯ�´�Ұ��ȥ�����ţ�������ǹʹ���Ρ��ƶ���һ����ǹ��˯�����ʵ��۾����������������˻𣬺�һ�һ��ȼ�ˡ�������ѽ��ѽ����˵�Ͻ�Ǯ�£��β������ϵ����������Ǻ�Ц��˵��ͷ��ͷ���㲻������ȥ��Ǯ����ͷ�������𣿺ٺ٣�˵����Ц��һ˫�����۶���ʱû�ˡ��ƶ�������dz��������ˣ�˵���ȶ��ҹ���ת���ɿ�����ݡ�С��������������ȫ����װ��������һ��С�ܴ����£��ӹ��β��������ľƺ���ھƣ�˳��ʯ��·��ɽ��ҡ��Ů������ӱߣ�����������Ӱ��Թ���ִ�ǹ�ִ�ǹ���ߣ������ϺŶ��ˣ������ڵ�����ɶǹ��������ˣ�Դ� �ȣ�����Щ��ս�˼����غ���զ������������������
����ɶ��Ӵ�������������Ҥ���Ǹ��������ֲ��Dz����á�
������צ���ֺ����æ���������գ�����֧ʹ�ˣ����ù�����ɻ
����˵Щɶ��Ӵ�������������£�˵�������˵ò��ˣ�����̧�Ի���ȥ�ˡ�
�����β�����Ц��˵��ͽ����߶��ͣ��ĸ������˸�������ٺ٣�
�����ƶ�����ȫ�������ĸ��֣����������Ƚ���ȫ���ֹ�ҵϵͳ���ܴ��ޱ����ù��ƻ��һ���ġ�
�����Ӱ�Ϫ�ֳ�����Ǯ��ɽ�µ��볧���������һ��ʯ���·˳��������ҡȥ���еĵط�ʯ��û�ˣ���ɵ���Ţ�ﲼ�����ѡ�ʱ�����磬���������֣�·���ټ����ˡ�ż����ӰŨ����γ��������������·�һ�㡣��������·�����ֹ�ҵϵͳ�ü������ӣ��鴮���������߰ڿ�����������˳����Χ�������е�ϸ���롢��ֽ������ҩ��ɰ���������ƣ������ռ���������볧�����볧�а���ʮ����ʷ���ճ���ϸ���룬����֬һ�㣬��ָһ�����������࣬�����ɲ�������ϰ���ǰ�������Թ����˱������ݣ����ؽ����£��������졢���ڡ���ţ����ֽ������ϸ�����ֲ�ֽ��������Χ����������������벻�õġ���ϸ�ֱ���ϸֽ�����˳�ˮ����������ý�ӣ�Ů��������Ь�������������Ͷ���������д�֡���Щ����ֽ������Ů�������벻�ã������ڰ�װ��С̯С����С������һ�㶼���š����¼����˻��Ķ࣬�̼ҽ����DZ������dzƺã�����ֽ���ˣ�������ͷ������ӡ����ǩ��ϯ�ݻ���˿һ����һ���Űںã�����ǩӳ�����Ƶ���ֽɷ�Ǻÿ���
��������ҡ��ĥ��Ϫ��Ϫ����ɽ����������̿���Ҥ����ǡ�����㵹Ҥ�������̳̳�ޡ��ײ���ˤ�Ƶ���������Ƭ���������¹������������������������Գ�������æµ�����֡��ߵ�ţ����ֽ����ȴ����ô�羹�к�Щ����·�ߴ����ӡ�·������������˴��ſ��ڸ��������۵Ļ�ţ���������������ݹ�������һȦȦ������ࡣת��ţ����ɽ���Ӿ�������������������������Ժ�Ӿ͵����볧�������˴����������Ȼ���ﺨ˯����һ���ܼ�һ�����Ŵ���æ�ţ���һ�����г����˸��������к����ƻ�ƺλ�ƣ�������Ҳ��������ѽ���ٺ٣��ƻ�ƺλ�ƣ�ȥ��ǹˣѽ���ٺ٣������ͺ����������ߣ����Ǹɲ������ӡ��ΰ۳���������Ļ�ƣ��ƶ�����ֽ���Ļ�ơ�
������ɽ��С·���п���˴�Ƹ���������Ϊ�볧�칫�صص�Ժ����ȥ��룬�����ߵ����£��볧������������ҡ�������������к�˵���������������ѽ���ٺ١�������������ֽ�̾������ӹ��̵��ϣ�Ц˵����ˣѽ��æ�ǣ����������ȫ�����ڼӰ��أ��Ǻǣ����˳�������磬�ӵ�һЦ��˵����������һ������һ�������������λ����ػ������˺ǣ���ɽ����û�������Եõ�Ұ�Ī��Ұ����������˹���������Ц��˵����ˣ�ģ��͵�ȥ��ɽ�������ŵ�����������Ͷ�Ц����Ц�������˻ƶ�������˵���ȣ��Ҹ���˵�Ǹ����أ�զ�����������ﲻ���ƶ�����֨��������һ�壬���һ����������û����ѽ�������볧�ĵ�Ȳ�������ֽ�����ƶ�����æ˵���ǣ���������˼��ֻ�ǡ���ֻ�ǡ���������һ��������Ц�����Ļƶ�����ͷ˵��С����Ī��Ī��������ˣ�ģ��������dz�����÷��㣬����Ҳ����������ס�㣬����Ҫ����Ū�����أ��β����۾������ɵõ����������ѽ���ƶ�����������˵�������¡���ȴ˵�����ؾְֳ���˵�ģ����ŵ��ſ����ƶ����������Ҫ���ǵ��ˡ�
����Ъ��������������������ɽ�������ΰ۳�һ·�������ߺ߲�ͣ��������ȥ���������䣺���ã����ã���ͷ�ϴ���ʲô��ǻ�Ӵ���ɻ��ֺ���ѽ���̨�塣
����������ɽ���֣�·��խ���������Ͷ��ˡ���ʱ̫���ѳ����ˣ���Ҳɢ�ò���ˣ��ͺӹ�����Ʈ����˿�������ӣ��ߴ���ɽ��Ҳ�����Ʋ����Ƶģ��ƾ��ƶ��������У���Ǯ�¶��͵����Ӻ��¶��ϵ����ӣ���ȥ�������ϵ���ɽ�����ţ�·�߲ݲݶ��Ͼ����ϵ�¶ˮ�ܿ�ʪ�˿��ȡ��ƶ���������˵����ȥ���ҲŲ�ȥ����β���գ��գ���ۣ�˵����������ĺ���Ӵ��զ��ȥ���ƶ���˵�����Ҳ�ȥ���β�����Ц�ˣ�§�����������ȵ�˵���Ҿ�������������ӣ���������զ�����ٺ٣�Īȥ���յij��������ɶ�ã���ɽ��������������ǹ����Ұζ���վ��𣿻ƶ��������Կ�˵�����ǡ����ǡ����У�����ֽ�����������ϸ��»�˵Ҫ���������أ�����ʱ�����ˣ�������զ���ң�
�����ƶ���˵��ȥ���������ȥ�˳�����º����ֹ�ҵ���������˵�� �β�����ֽ���ӻƶ����Ĺ��������죬���������꣬�ƶ���˵���ߣ������������������β��������۶�ʱЦ��һ���죬˵���Ǹ���ͣ��Ǹþ��͡��ƶ�����Ů�˰��ϴ��ڽ�Ǯ��ɽ�ϴ��ֻ����������ֳ����̻����ף����������˶Ժȡ��β����Ǹ����ɣ�ֻҪ���˾�һ������̫��ʺ���廨����Ц��ϡ�ã���Ҳ�ࡣ����ȴ�����úܣ�Ҳ��˵��Ҳ��Ц�������ԿǺȾơ��ƶ���Ҳ�����ԿǺȾơ�Ů�˾�����ʲô�����������˳����������Ϸ��ˣ�Χ���ϲ����֣�Ц˵���λ�ƣ����������ˣ������˵�������Ǵ����ɿ�ģ����ɿ㴩��������ݿɶ�����Ӵ���������β��������Կǣ�˵Ҫ��Ҫ�ã���ͷ��ͷ���������ˣ�Ů���ܾ����ö�����æ������ȥ�ˡ��ϴ��϶����������ſ������˿��ֺ�����Ժ���ʳ��һ˫�۾�����������빷�����ƶ���������ͬ�β���һ�������ˣ����Ͼƣ������̵ݹ�ȥ���������ϻ���̡��ƶ������˺β���һ�ۣ��������ɵ�����һЦ��˵��ʵҲû��ɶ�ӣ��ֲ�����Զ��Զ�������п��һ�������Ⱦƴ�ǹ����Ҫȥ��Ǯ����ͷ��Ƭ���ִ��������ȣ���˵������Ұ�����ǽ�Ǯ��ѽ���չ֣�զ��������ҧ�ˣ�һǹ��ȥ�������ˣ��β�����������������������ЦЦ�������ûƶ�������������һ��С������˿��ͷ���ƶ���šü�ƺȣ������㣡���������Ź�ͷ�ij���ȥ���β������˿��̣�������˵�����Ⱦƴ�ǹ����û�˸�����Ӵ���������ӣ��⳧�dz�����������ȫ����һ�ٶ����������æ�ù��ӷ��죿�ƶ�������Ϊ���ЦЦ���β�������˵��������������С�����żҶ������г���Ϣ����С�Ǹ���ҵ����ơ������dz�����ΡΡ�ģ�����������ͷ�����ĵģ�ʪʪ�ģ���ޡ�
�����β����滹û˵�����ƶ���һ���������æ��ĥ��������תת���Ļ���ʱ����ȥ��ǹ�Ⱦƣ��β��������ⲻ�˳��ﴮ������ÿ�ض����ƶ��������˶��������С�����һ����û�����۾��Ͳ�ʱ���˱�������ɨ��֪���Ǵ�æ�ˣ�һ��Ը��̾������ˡ�
����Ҳ�����⡣һ�غβ������ǣ��������պ�Ҫ�°��ˣ��ƶ������ѽ��˱�������������˵�����ߣ�����������վ�ȥ���β�����ûȥ�����ң�Ҳ��ȥ�����ƶ����������ӡ������ֹܾ֣����˻ƶ����������ߣ����ξ��֡����Ŷ����ۿ�Ҫ�����ˣ��β��������������ߣ��ʻ��к�Զ�ǣ��ƶ���̧��ָָ�����̶���ţ��ջ���и�¥�Ǻ������ӣ�˵���ˡ��β�������ţ������䴮�б����Ӱ��ƿ����ٽֵ�һ����������Ϳ�����һ�ŵ��������ľ����ֻ�������棬һ����˱�ͷǽ�ϳ�����һ�㡣һ����ͷ�̴��£���������ͷ�������ָ����������һ��Ⱥ����һ����תת�������ƶ�������ֽ�̵ݹ�ȥ��˵�����������˵��Χ��һ˩����������˴Ӳƾ�������Ľ�ɫת������˳·��ص�����������������ת��ȥ��ǰ���𣬶˿���������ϸ��Ŵֲ��˴ֲ��ú̿�����ϻ����Ϲ����˴��������ȣ���������Ũ�̹������벻���ƶ������ӹ�����������˵���������Ҳ����ë���ҵú�û�����ӵ��������ƶ���Ů���Ǹ�ҩ�ޣ����ڳǹ���֯���ϰ࣬�Ӱ�ӵ㵷Ū�Ƶ���ʱ����֯���������������һӦ����ȫ�������ˡ��β������ƶ�������������ȿ�ǺǺ��ǰæ���˵����������ˣ�����̾Ϣ�����̿������ų��˸��̾����ˡ�
���������β����ٲ�ȥ�ƶ����ң����ǰ������£��������м���Ǯ���ͳ��˻ƶ���ȥС�ƹ���������
�����ƶ������лذ�Ϫ�Һβ����Ⱦƣ������ĸ�ʱ�����ˡ����괺�ϣ��ƶ����ܳ��Ƕ��䶷���ϼ����´���������Ƶûţ���������Ϫתת��˦�������˶���ʮ��С·���ӻ���Ϫ���ӣ���ʯ���·�Ѿ��ij��˻�����·��˳��·ҡ��ţ����ֽ�����ǰ�����ʱ�֡�ȴ�����ﳧ���������壬û����·�ߴ����ӵĴ�������û�˴��ſ���������ʹţ������ģ�û��ͣ�ӱ���ͷ����װֽ�����������ɽ������ֽ�����أ�Ժ����������һ����Ӱȫ�ޡ����˵�ֵ����˶�����ȥ������ų���Ժ�ߡ�
������Ժ��ԭ�Ǹ���˽լ������������һ�����أ�˳ɽ�Ʋ��ݽ���ҡ��ͨ����ͷ��Ժ�Ĺ������Բ����ˡ��ͳ������ߺ�ȣ�˵�ȣ�զ�˻�������û�ø��������������������������Ժ�м仨�Կ����IJ˵��DZ����˴�Ӧ�����žͼ�����Ǯ�ձ�����һ�ᶵ��ư���˴ӹ�����״Ԫ����Ƴ��������˻ƶ�������ϲ��ͨ��Ź⣬��������������һ��һ��ҡ�������ƶ��������̾��������˼���������أ�����ȥ�ˣ�Ǯ�ձ����۰����̣�̾˵��ɢ�ˡ���ɢ�ˡ�����췴���صĻؼң�ɢ�����ˣ����ʺΰ۳��أ���˵�������ã���ƽʱҲ�������ģ�����ͺ����۴�����ֻҰ����������������������������������ү����������ս���������У���������һ�����ˣ�����̯����ء�˵��ָ����ͷˮ���ְ����ŵĻ���ҡ�
�����ᵽ��ǹ�ƶ���������������ʯ�����������������㷿Ժ���ƿ�������ţ���ζ��ζ���û������ֻ���β��������˲�̯�������ϣ���Ƥ�ϴ��Ŵ��������������ɽ�졣��Ц���������ӽа��죬�β����Ż����������������汧Թ���ϳ��ǻƶ���Ұ��ҧ��������˵զ��զ�����������Ҳ���·��ۣ���˵��һ������ã�һ���ǹ�ɾƶ�á���˵��������û��ǹҩ�ˣ����ǻ�ϲ�õ��˶���
����û��ǹҩҲ�Ѳ�ס���������ų��������̰��˻�������β�����˵�ߣ��º�����ԣ�˵�ţ�����ƿ�ƴ��Żƶ���ȥ��������������ү����ȥ���档�ƶ�������һ����֪����ʿ������ү���ϵõģ�����û˵�ʹ����������˺ӡ�
������ү���������볧���º��壬˵���������ˡ����������ŷ���������֨��֨�µ����Ž��������ź��嵴�˸������Σ���������֩����˿���³�������������������ү����������Ҷ���̸ˣ�������һ�����˻���̡�����Ҳ�����̳ԣ���һ��ûһ��ͬ��ү�������������ڻ����������������ڻ����������������������������������ٻ��������С���ȵ��㣬������ϲ�ú�ͯ������ү��˵���ߣ����ݺ��������ȥ��
������ʱ̫���Ѿ���ɽ��������ΡΡɽˮ���������������������ˮ��ӳ��Ũī���ڳγΣ�����ȴ���������ϼӳ������ͷס����а�ɫˮ���������������ƣ�Զ���������̵���´���������ţƤ���ڽ���ĥ��������֨��֨��������Ƭ��ˮ�������ﴫ����һ��������ңԶ���������������ӵ���ϼɢ���־��ţ��ӷ���������ĵĴ���������������ƶ��������ۿ�������Ϥ���������������ʹ��ˡ�
�������ݺ��ѽ��ұߣ���ү���������ˣ��ų��������������ﱧ�����ݲ�̳���ɵ�С¯��Ŵ�β���հ���ȡ����װ�˲��������裬�����һ�Ѱ�ץ���ڴ����ϣ�����¯���������������ɴ��ɴ������ӵ��ϻ�ɲʱ���������������ơ�
�����ƶ�����ȥ�ﲮү�ջ𣬼������������ѻ���Ϩ����ү��Ц��˵�������ɶ���������ĸ����յ����ģ��������ˣ�����ˣȥ�ɣ��ƶ���Ĩ��ͷ���ϲ�ң��ͳ��˺β���˵�ߣ��ݺ�����תתȥ��Ҫ������������⣬һ���ӿ���Ҳû��������
�������������˰����ֽŲ��þ�ƨ���������ϵ�����ǰ����ֻ�������Ʋ����ƵĽ�Ǯ�����ӷ·���ͷ���������������ʮ��������������ɽ������������ý�������ն�ϣ�����ʯ��ɽ�İ�����ɭɭ�εض�����ӥ������ǰ������һ�������˾�����״�ع��ͱ��ϡ���һ��������³���ɽ�ڴ����ӣ�Ҫ���Ĵ����������������װ��������������Ĵ�˵��վ����һ��������������ضε���Ҫ�������Ͷ����컯��ΰ���������������ˡ�
�����������ת���������֪�������Ѻڵú�Ϳ�����ò�ү�к���������С�������Żص����ϡ�
���������������洬���ϵ���Ⱦƣ��������ε�ɽ����ˮ����һ��ûһ��˵�ŵ���ֱ�ȵ������졣
������ϧ�����������Ӳ��࣬��ϧ�����DZ��������¶�˩�ŵģ�֮��ƶ�����û�ع���Ϫ����û���������ַ���֮�Ρ�
����������ʮ����ɣ��β���ͻȻ�����ˡ��β�����ʱ���ƶ�������Ҫ��ȥ�����µģ��ɽӵ�������շת�����Ŀ��ţ��Ѿ���ȥ�˰��£���������Ѿ�������ȥ��������һȺ����������С��ͽ�����ˣ�Ҳ��ֻ���ļ��ˡ�
��������ֽ��������������������˵�β����Ǻ��������ġ���֪������ȴ����˵����ɶ����ǣ�����ֻ�Ǹ����ӣ������ǹ����վƸɶ��ˣ����վƻ��������Ҥ���Ļ����צ��˵��Ҳ���־ƣ�Ҳ���ֲ������dz����ģ�����������أ��볧�������ϳ���˵��
�����ϳ����Ѿ��ϵ�ή����������ɽ���ص��س��оӡ�����û�£���������ȶ����ܰ�˳�������������ͬ�˰ڰ��������������Ǽ��䣬���������Ӷ������ǣ���ɳ�ģ�����ģ���Ҥ�ģ����װ���ġ������˾����˾Ͷ�������
�����ϳ������ûƶ���ͬ�β����õò����ˣ������ҵ��˻��ڴ�������ǰ�����������ϸ˵ԭί��˵�Ǻβ�������ʱ�ں���ֽ��������������˿����������һ��Ҫ����ֽ����ʢ������ʱ������ã�С���������̳̳����ֽ��ֽ����������ũҩ��ƥ��װƤЬ��Ȼ�������ֻҪ���������Ͳ�����·���ֹ�ҵϵͳ����һ��¿�������Ȼ��졣˭֪�þ���������ص�ͬ���Ʒ�ܿ켷�˽������˼ҵĹ����¹�ģ��ɱ��������ã��ݿ�����һ��ܿ�ռ������г��������ֹ������Ķ�����Ҳ�����ʽ���������ˣ��IJ�����ˣ����ɳ�����ˣ�ȫ���ֹ�ҵϵͳ�ϰٸ�������������һҹ֮����˶�룡ʣ�������г����볧ũ���������ϵı�֯�������ϳ�ʮ������λ����һ�ټ�һ�ٹ��Ӳд���ֽ������û��˶������������Ҳ�ǹŵ�����������˵���Ҳ����һ�仰���¶���
����ֽ�����»ƶ�����֪���ģ������о���������ŵģ��Ǻβ���һ�δ������ң�˵�ٸ���һ����أ�˵���������ݴ���˵����ͷ�и�����Ŀ��ֻҪ�������Ͷ�ʣ���ȥ�˿϶��������������ƶ������ǵúβ���̸����������Ŀ���۷Ź��ĭ��ɵ��������ƶ�����ֽ�����и���ģ����Ǻβ�����������ֻҪ��һ�ǵ���������ֺγ�Ը�⿴��ֽ�����գ��ɻƶ������������ļҵף���ʲô�ͽ�ֽȦͲʽ����ֽ���ö���Ͷ�ʣ����﹤�ʶ�����������Ǯ���ɻƶ�������������ˮ���л��ỹ����˵������
�����ϳ���˵�������Ӻβ�������ħ���ϴ��������ݹ��ص�����Ŀ�����������ܴ�������Լ�������ߵ��Ķ���������������ֽ���Ͳ���˭�����İ����ѻ���ɽ�Ŀ��һ������ȥ���ò����㵽�����˵��Ҫ����������ֽ�ˣ���ת��֮��ȦͲʽ����ֽ��ؿ������������ͬ��Լ����Ҫͬ������һ�����β�����Ϫ�ֳ�תһȦ��������ҡ�س��һ��Ⱥ��������Χ��ȥ����Ҫ���ʣ�Թ������ģ��������ֵģ������ٲ�������Ҫ���������Ůȥ���ҳԷ��ģ����÷��졣����Ҿ��ͷ�ô���Ȼ�ȥ�����Ƶ������Ⱥ������칫�ң����������һ���˵���˵��������������ʡ���һ��ë�ˣ�����ˣ��Ƥ����û�ã�ҪǮû�ã�Ҫ��һ������Ƹ�ת�����������ִ������ܽ�ȥ��˵��һ���¶����豸������ͷ��ծ�������ˣ�����Ǯ�����豸��ծ�������Ǹ����������ӣ���˵�˼Ұ������������ˣ��Ļ��ŵ�ס��ֻ������ҧ���������ϵ������������˼���ɶ��ѽɶ��ѽ��������һ������һ����Ѫ��ǹ����������˾������˵ص���ȥ�ˡ���
������ʵ�����¶��ƶ���Ҳ���ø���ţ�ֻ��û�ϳ���˵��������ϸ����������ȥ����ǰ�������ƶ����������ĬĬ�����̾���������˵�����˾���̫���ǿ���ֲ�ʶʱ����ʵ������ǿ������Ҳ�Ȳ���ֽ������Ҫ����������û���ۺ�ľ��������������Ź֣���ֻ��ֽ�����ҿ������ֹ�ҵ��û������������ˣ��ƶ������ȵؿ����ϳ�������Ȼ��Ҳ��������Ԥ�У���������Dz�Ը���ϣ����ϳ���һ���ӵ��������ʱ�������Dz���֮�ס�
��������ƶ������������ˡ��������˴���꣬���������ʮ�����Ѹ���Ϊ���Ṥҵ�ֵ�ԭ�ֹܾ֣�������λһ��������ŵ���������գ�ֻʣ�˸��ռ��ӵĶ�������dzŲ�����ά���˼�����Ҳ�ʹ���������ϳ��׳����ˡ��ƶ������ݺ��ڻ��ʦ������ı�˸�ְλ�������ȣ�һ���и���Ϫ�����IJ��£����źþ�ûȥ�Ƿ��ˣ�����ȡ���������˰�Ϫ�������£����β�������ȥ�������¡��뿪ʱ���β���Ů�˽�һ������ˮ�����ƶ������˵���������롣�ƶ����ο��������ᣬ���йɾ�ζ���ֵ��볧��ţ������ֽ����ַת��ת����������п����벻���Լ�Ϊ֮�ܶ���һ������ҵ����ͷ������ȦȦ��ҡͷ̾Ϣ֮�࣬��������ֽ�����ӻ������������ȥ����û�ҵ���
�������ߣ����Ľ��������ƺӣ������ߣ����ң�����֪�࣬���ˡ������쵼���ֹ�ְ���ʸִ�ý�����ʸ��ձ��硣
������ַ���Ĵ�ʡ��֦�����ʸִ�ý�����ʸ��ձ���
�����ʱࣺ617067
�����绰����0812��3381849��
�����ֻ���13882364982
��������Ӧ������ȡ���ȣ��ƶ�������Ұ��ȥ�ǣ�
������֪���ƶ�������ǹ��һ˵��ɽ��Ұ�����������ز����ˣ������ǹص���˿�Ϸ졣��·��Ժ��Ҫ����ʮ��ʯ���ݶ��������������������ž���ˮ����˳�����ο����ӣ����˿��վơ����ú��죬���ֱ������һĨ��������ǹ��ĸ���һ�𣬱��𣬻ƶ��������վƴ�ǹ�ǣ�����Ժͷ�Ǻ�����ľ���е�����Ӧ��������������������ţ��ΰ��ӱ߿������¿��ӿ����������Կ�һ˦����һ��̵���Աߣ���Թ˵��Ӳ�ǣ��Ͷ�����զ��������ѳ��ͺ��������˯û˯�ѣ������ݻ��ˡ��β�����������һ������̫��ʺ��������Ц�ã�˵�˯��ɶ˯ͷ����������˯���٣��ߣ���ǹȥ���Ͻ�Ǯ�´�Ұ��ȥ�����ţ�������ǹʹ���Ρ��ƶ���һ����ǹ��˯�����ʵ��۾����������������˻𣬺�һ�һ��ȼ�ˡ�������ѽ��ѽ����˵�Ͻ�Ǯ�£��β������ϵ����������Ǻ�Ц��˵��ͷ��ͷ���㲻������ȥ��Ǯ����ͷ�������𣿺ٺ٣�˵����Ц��һ˫�����۶���ʱû�ˡ��ƶ�������dz��������ˣ�˵���ȶ��ҹ���ת���ɿ�����ݡ�С��������������ȫ����װ��������һ��С�ܴ����£��ӹ��β��������ľƺ���ھƣ�˳��ʯ��·��ɽ��ҡ��Ů������ӱߣ�����������Ӱ��Թ���ִ�ǹ�ִ�ǹ���ߣ������ϺŶ��ˣ������ڵ�����ɶǹ��������ˣ�Դ� �ȣ�����Щ��ս�˼����غ���զ������������������
����ɶ��Ӵ�������������Ҥ���Ǹ��������ֲ��Dz����á�
������צ���ֺ����æ���������գ�����֧ʹ�ˣ����ù�����ɻ
����˵Щɶ��Ӵ�������������£�˵�������˵ò��ˣ�����̧�Ի���ȥ�ˡ�
�����β�����Ц��˵��ͽ����߶��ͣ��ĸ������˸�������ٺ٣�
�����ƶ�����ȫ�������ĸ��֣����������Ƚ���ȫ���ֹ�ҵϵͳ���ܴ��ޱ����ù��ƻ��һ���ġ�
�����Ӱ�Ϫ�ֳ�����Ǯ��ɽ�µ��볧���������һ��ʯ���·˳��������ҡȥ���еĵط�ʯ��û�ˣ���ɵ���Ţ�ﲼ�����ѡ�ʱ�����磬���������֣�·���ټ����ˡ�ż����ӰŨ����γ��������������·�һ�㡣��������·�����ֹ�ҵϵͳ�ü������ӣ��鴮���������߰ڿ�����������˳����Χ�������е�ϸ���롢��ֽ������ҩ��ɰ���������ƣ������ռ���������볧�����볧�а���ʮ����ʷ���ճ���ϸ���룬����֬һ�㣬��ָһ�����������࣬�����ɲ�������ϰ���ǰ�������Թ����˱������ݣ����ؽ����£��������졢���ڡ���ţ����ֽ������ϸ�����ֲ�ֽ��������Χ����������������벻�õġ���ϸ�ֱ���ϸֽ�����˳�ˮ����������ý�ӣ�Ů��������Ь�������������Ͷ���������д�֡���Щ����ֽ������Ů�������벻�ã������ڰ�װ��С̯С����С������һ�㶼���š����¼����˻��Ķ࣬�̼ҽ����DZ������dzƺã�����ֽ���ˣ�������ͷ������ӡ����ǩ��ϯ�ݻ���˿һ����һ���Űںã�����ǩӳ�����Ƶ���ֽɷ�Ǻÿ���
��������ҡ��ĥ��Ϫ��Ϫ����ɽ����������̿���Ҥ����ǡ�����㵹Ҥ�������̳̳�ޡ��ײ���ˤ�Ƶ���������Ƭ���������¹������������������������Գ�������æµ�����֡��ߵ�ţ����ֽ����ȴ����ô�羹�к�Щ����·�ߴ����ӡ�·������������˴��ſ��ڸ��������۵Ļ�ţ���������������ݹ�������һȦȦ������ࡣת��ţ����ɽ���Ӿ�������������������������Ժ�Ӿ͵����볧�������˴����������Ȼ���ﺨ˯����һ���ܼ�һ�����Ŵ���æ�ţ���һ�����г����˸��������к����ƻ�ƺλ�ƣ�������Ҳ��������ѽ���ٺ٣��ƻ�ƺλ�ƣ�ȥ��ǹˣѽ���ٺ٣������ͺ����������ߣ����Ǹɲ������ӡ��ΰ۳���������Ļ�ƣ��ƶ�����ֽ���Ļ�ơ�
������ɽ��С·���п���˴�Ƹ���������Ϊ�볧�칫�صص�Ժ����ȥ��룬�����ߵ����£��볧������������ҡ�������������к�˵���������������ѽ���ٺ١�������������ֽ�̾������ӹ��̵��ϣ�Ц˵����ˣѽ��æ�ǣ����������ȫ�����ڼӰ��أ��Ǻǣ����˳�������磬�ӵ�һЦ��˵����������һ������һ�������������λ����ػ������˺ǣ���ɽ����û�������Եõ�Ұ�Ī��Ұ����������˹���������Ц��˵����ˣ�ģ��͵�ȥ��ɽ�������ŵ�����������Ͷ�Ц����Ц�������˻ƶ�������˵���ȣ��Ҹ���˵�Ǹ����أ�զ�����������ﲻ���ƶ�����֨��������һ�壬���һ����������û����ѽ�������볧�ĵ�Ȳ�������ֽ�����ƶ�����æ˵���ǣ���������˼��ֻ�ǡ���ֻ�ǡ���������һ��������Ц�����Ļƶ�����ͷ˵��С����Ī��Ī��������ˣ�ģ��������dz�����÷��㣬����Ҳ����������ס�㣬����Ҫ����Ū�����أ��β����۾������ɵõ����������ѽ���ƶ�����������˵�������¡���ȴ˵�����ؾְֳ���˵�ģ����ŵ��ſ����ƶ����������Ҫ���ǵ��ˡ�
����Ъ��������������������ɽ�������ΰ۳�һ·�������ߺ߲�ͣ��������ȥ���������䣺���ã����ã���ͷ�ϴ���ʲô��ǻ�Ӵ���ɻ��ֺ���ѽ���̨�塣
����������ɽ���֣�·��խ���������Ͷ��ˡ���ʱ̫���ѳ����ˣ���Ҳɢ�ò���ˣ��ͺӹ�����Ʈ����˿�������ӣ��ߴ���ɽ��Ҳ�����Ʋ����Ƶģ��ƾ��ƶ��������У���Ǯ�¶��͵����Ӻ��¶��ϵ����ӣ���ȥ�������ϵ���ɽ�����ţ�·�߲ݲݶ��Ͼ����ϵ�¶ˮ�ܿ�ʪ�˿��ȡ��ƶ���������˵����ȥ���ҲŲ�ȥ����β���գ��գ���ۣ�˵����������ĺ���Ӵ��զ��ȥ���ƶ���˵�����Ҳ�ȥ���β�����Ц�ˣ�§�����������ȵ�˵���Ҿ�������������ӣ���������զ�����ٺ٣�Īȥ���յij��������ɶ�ã���ɽ��������������ǹ����Ұζ���վ��𣿻ƶ��������Կ�˵�����ǡ����ǡ����У�����ֽ�����������ϸ��»�˵Ҫ���������أ�����ʱ�����ˣ�������զ���ң�
�����ƶ���˵��ȥ���������ȥ�˳�����º����ֹ�ҵ���������˵�� �β�����ֽ���ӻƶ����Ĺ��������죬���������꣬�ƶ���˵���ߣ������������������β��������۶�ʱЦ��һ���죬˵���Ǹ���ͣ��Ǹþ��͡��ƶ�����Ů�˰��ϴ��ڽ�Ǯ��ɽ�ϴ��ֻ����������ֳ����̻����ף����������˶Ժȡ��β����Ǹ����ɣ�ֻҪ���˾�һ������̫��ʺ���廨����Ц��ϡ�ã���Ҳ�ࡣ����ȴ�����úܣ�Ҳ��˵��Ҳ��Ц�������ԿǺȾơ��ƶ���Ҳ�����ԿǺȾơ�Ů�˾�����ʲô�����������˳����������Ϸ��ˣ�Χ���ϲ����֣�Ц˵���λ�ƣ����������ˣ������˵�������Ǵ����ɿ�ģ����ɿ㴩��������ݿɶ�����Ӵ���������β��������Կǣ�˵Ҫ��Ҫ�ã���ͷ��ͷ���������ˣ�Ů���ܾ����ö�����æ������ȥ�ˡ��ϴ��϶����������ſ������˿��ֺ�����Ժ���ʳ��һ˫�۾�����������빷�����ƶ���������ͬ�β���һ�������ˣ����Ͼƣ������̵ݹ�ȥ���������ϻ���̡��ƶ������˺β���һ�ۣ��������ɵ�����һЦ��˵��ʵҲû��ɶ�ӣ��ֲ�����Զ��Զ�������п��һ�������Ⱦƴ�ǹ����Ҫȥ��Ǯ����ͷ��Ƭ���ִ��������ȣ���˵������Ұ�����ǽ�Ǯ��ѽ���չ֣�զ��������ҧ�ˣ�һǹ��ȥ�������ˣ��β�����������������������ЦЦ�������ûƶ�������������һ��С������˿��ͷ���ƶ���šü�ƺȣ������㣡���������Ź�ͷ�ij���ȥ���β������˿��̣�������˵�����Ⱦƴ�ǹ����û�˸�����Ӵ���������ӣ��⳧�dz�����������ȫ����һ�ٶ����������æ�ù��ӷ��죿�ƶ�������Ϊ���ЦЦ���β�������˵��������������С�����żҶ������г���Ϣ����С�Ǹ���ҵ����ơ������dz�����ΡΡ�ģ�����������ͷ�����ĵģ�ʪʪ�ģ���ޡ�
�����β����滹û˵�����ƶ���һ���������æ��ĥ��������תת���Ļ���ʱ����ȥ��ǹ�Ⱦƣ��β��������ⲻ�˳��ﴮ������ÿ�ض����ƶ��������˶��������С�����һ����û�����۾��Ͳ�ʱ���˱�������ɨ��֪���Ǵ�æ�ˣ�һ��Ը��̾������ˡ�
����Ҳ�����⡣һ�غβ������ǣ��������պ�Ҫ�°��ˣ��ƶ������ѽ��˱�������������˵�����ߣ�����������վ�ȥ���β�����ûȥ�����ң�Ҳ��ȥ�����ƶ����������ӡ������ֹܾ֣����˻ƶ����������ߣ����ξ��֡����Ŷ����ۿ�Ҫ�����ˣ��β��������������ߣ��ʻ��к�Զ�ǣ��ƶ���̧��ָָ�����̶���ţ��ջ���и�¥�Ǻ������ӣ�˵���ˡ��β�������ţ������䴮�б����Ӱ��ƿ����ٽֵ�һ����������Ϳ�����һ�ŵ��������ľ����ֻ�������棬һ����˱�ͷǽ�ϳ�����һ�㡣һ����ͷ�̴��£���������ͷ�������ָ����������һ��Ⱥ����һ����תת�������ƶ�������ֽ�̵ݹ�ȥ��˵�����������˵��Χ��һ˩����������˴Ӳƾ�������Ľ�ɫת������˳·��ص�����������������ת��ȥ��ǰ���𣬶˿���������ϸ��Ŵֲ��˴ֲ��ú̿�����ϻ����Ϲ����˴��������ȣ���������Ũ�̹������벻���ƶ������ӹ�����������˵���������Ҳ����ë���ҵú�û�����ӵ��������ƶ���Ů���Ǹ�ҩ�ޣ����ڳǹ���֯���ϰ࣬�Ӱ�ӵ㵷Ū�Ƶ���ʱ����֯���������������һӦ����ȫ�������ˡ��β������ƶ�������������ȿ�ǺǺ��ǰæ���˵����������ˣ�����̾Ϣ�����̿������ų��˸��̾����ˡ�
���������β����ٲ�ȥ�ƶ����ң����ǰ������£��������м���Ǯ���ͳ��˻ƶ���ȥС�ƹ���������
�����ƶ������лذ�Ϫ�Һβ����Ⱦƣ������ĸ�ʱ�����ˡ����괺�ϣ��ƶ����ܳ��Ƕ��䶷���ϼ����´���������Ƶûţ���������Ϫתת��˦�������˶���ʮ��С·���ӻ���Ϫ���ӣ���ʯ���·�Ѿ��ij��˻�����·��˳��·ҡ��ţ����ֽ�����ǰ�����ʱ�֡�ȴ�����ﳧ���������壬û����·�ߴ����ӵĴ�������û�˴��ſ���������ʹţ������ģ�û��ͣ�ӱ���ͷ����װֽ�����������ɽ������ֽ�����أ�Ժ����������һ����Ӱȫ�ޡ����˵�ֵ����˶�����ȥ������ų���Ժ�ߡ�
������Ժ��ԭ�Ǹ���˽լ������������һ�����أ�˳ɽ�Ʋ��ݽ���ҡ��ͨ����ͷ��Ժ�Ĺ������Բ����ˡ��ͳ������ߺ�ȣ�˵�ȣ�զ�˻�������û�ø��������������������������Ժ�м仨�Կ����IJ˵��DZ����˴�Ӧ�����žͼ�����Ǯ�ձ�����һ�ᶵ��ư���˴ӹ�����״Ԫ����Ƴ��������˻ƶ�������ϲ��ͨ��Ź⣬��������������һ��һ��ҡ�������ƶ��������̾��������˼���������أ�����ȥ�ˣ�Ǯ�ձ����۰����̣�̾˵��ɢ�ˡ���ɢ�ˡ�����췴���صĻؼң�ɢ�����ˣ����ʺΰ۳��أ���˵�������ã���ƽʱҲ�������ģ�����ͺ����۴�����ֻҰ����������������������������������ү����������ս���������У���������һ�����ˣ�����̯����ء�˵��ָ����ͷˮ���ְ����ŵĻ���ҡ�
�����ᵽ��ǹ�ƶ���������������ʯ�����������������㷿Ժ���ƿ�������ţ���ζ��ζ���û������ֻ���β��������˲�̯�������ϣ���Ƥ�ϴ��Ŵ��������������ɽ�졣��Ц���������ӽа��죬�β����Ż����������������汧Թ���ϳ��ǻƶ���Ұ��ҧ��������˵զ��զ�����������Ҳ���·��ۣ���˵��һ������ã�һ���ǹ�ɾƶ�á���˵��������û��ǹҩ�ˣ����ǻ�ϲ�õ��˶���
����û��ǹҩҲ�Ѳ�ס���������ų��������̰��˻�������β�����˵�ߣ��º�����ԣ�˵�ţ�����ƿ�ƴ��Żƶ���ȥ��������������ү����ȥ���档�ƶ�������һ����֪����ʿ������ү���ϵõģ�����û˵�ʹ����������˺ӡ�
������ү���������볧���º��壬˵���������ˡ����������ŷ���������֨��֨�µ����Ž��������ź��嵴�˸������Σ���������֩����˿���³�������������������ү����������Ҷ���̸ˣ�������һ�����˻���̡�����Ҳ�����̳ԣ���һ��ûһ��ͬ��ү�������������ڻ����������������ڻ����������������������������������ٻ��������С���ȵ��㣬������ϲ�ú�ͯ������ү��˵���ߣ����ݺ��������ȥ��
������ʱ̫���Ѿ���ɽ��������ΡΡɽˮ���������������������ˮ��ӳ��Ũī���ڳγΣ�����ȴ���������ϼӳ������ͷס����а�ɫˮ���������������ƣ�Զ���������̵���´���������ţƤ���ڽ���ĥ��������֨��֨��������Ƭ��ˮ�������ﴫ����һ��������ңԶ���������������ӵ���ϼɢ���־��ţ��ӷ���������ĵĴ���������������ƶ��������ۿ�������Ϥ���������������ʹ��ˡ�
�������ݺ��ѽ��ұߣ���ү���������ˣ��ų��������������ﱧ�����ݲ�̳���ɵ�С¯��Ŵ�β���հ���ȡ����װ�˲��������裬�����һ�Ѱ�ץ���ڴ����ϣ�����¯���������������ɴ��ɴ������ӵ��ϻ�ɲʱ���������������ơ�
�����ƶ�����ȥ�ﲮү�ջ𣬼������������ѻ���Ϩ����ү��Ц��˵�������ɶ���������ĸ����յ����ģ��������ˣ�����ˣȥ�ɣ��ƶ���Ĩ��ͷ���ϲ�ң��ͳ��˺β���˵�ߣ��ݺ�����תתȥ��Ҫ������������⣬һ���ӿ���Ҳû��������
�������������˰����ֽŲ��þ�ƨ���������ϵ�����ǰ����ֻ�������Ʋ����ƵĽ�Ǯ�����ӷ·���ͷ���������������ʮ��������������ɽ������������ý�������ն�ϣ�����ʯ��ɽ�İ�����ɭɭ�εض�����ӥ������ǰ������һ�������˾�����״�ع��ͱ��ϡ���һ��������³���ɽ�ڴ����ӣ�Ҫ���Ĵ����������������װ��������������Ĵ�˵��վ����һ��������������ضε���Ҫ�������Ͷ����컯��ΰ���������������ˡ�
�����������ת���������֪�������Ѻڵú�Ϳ�����ò�ү�к���������С�������Żص����ϡ�
���������������洬���ϵ���Ⱦƣ��������ε�ɽ����ˮ����һ��ûһ��˵�ŵ���ֱ�ȵ������졣
������ϧ�����������Ӳ��࣬��ϧ�����DZ��������¶�˩�ŵģ�֮��ƶ�����û�ع���Ϫ����û���������ַ���֮�Ρ�
����������ʮ����ɣ��β���ͻȻ�����ˡ��β�����ʱ���ƶ�������Ҫ��ȥ�����µģ��ɽӵ�������շת�����Ŀ��ţ��Ѿ���ȥ�˰��£���������Ѿ�������ȥ��������һȺ����������С��ͽ�����ˣ�Ҳ��ֻ���ļ��ˡ�
��������ֽ��������������������˵�β����Ǻ��������ġ���֪������ȴ����˵����ɶ����ǣ�����ֻ�Ǹ����ӣ������ǹ����վƸɶ��ˣ����վƻ��������Ҥ���Ļ����צ��˵��Ҳ���־ƣ�Ҳ���ֲ������dz����ģ�����������أ��볧�������ϳ���˵��
�����ϳ����Ѿ��ϵ�ή����������ɽ���ص��س��оӡ�����û�£���������ȶ����ܰ�˳�������������ͬ�˰ڰ��������������Ǽ��䣬���������Ӷ������ǣ���ɳ�ģ�����ģ���Ҥ�ģ����װ���ġ������˾����˾Ͷ�������
�����ϳ������ûƶ���ͬ�β����õò����ˣ������ҵ��˻��ڴ�������ǰ�����������ϸ˵ԭί��˵�Ǻβ�������ʱ�ں���ֽ��������������˿����������һ��Ҫ����ֽ����ʢ������ʱ������ã�С���������̳̳����ֽ��ֽ����������ũҩ��ƥ��װƤЬ��Ȼ�������ֻҪ���������Ͳ�����·���ֹ�ҵϵͳ����һ��¿�������Ȼ��졣˭֪�þ���������ص�ͬ���Ʒ�ܿ켷�˽������˼ҵĹ����¹�ģ��ɱ��������ã��ݿ�����һ��ܿ�ռ������г��������ֹ������Ķ�����Ҳ�����ʽ���������ˣ��IJ�����ˣ����ɳ�����ˣ�ȫ���ֹ�ҵϵͳ�ϰٸ�������������һҹ֮����˶�룡ʣ�������г����볧ũ���������ϵı�֯�������ϳ�ʮ������λ����һ�ټ�һ�ٹ��Ӳд���ֽ������û��˶������������Ҳ�ǹŵ�����������˵���Ҳ����һ�仰���¶���
����ֽ�����»ƶ�����֪���ģ������о���������ŵģ��Ǻβ���һ�δ������ң�˵�ٸ���һ����أ�˵���������ݴ���˵����ͷ�и�����Ŀ��ֻҪ�������Ͷ�ʣ���ȥ�˿϶��������������ƶ������ǵúβ���̸����������Ŀ���۷Ź��ĭ��ɵ��������ƶ�����ֽ�����и���ģ����Ǻβ�����������ֻҪ��һ�ǵ���������ֺγ�Ը�⿴��ֽ�����գ��ɻƶ������������ļҵף���ʲô�ͽ�ֽȦͲʽ����ֽ���ö���Ͷ�ʣ����﹤�ʶ�����������Ǯ���ɻƶ�������������ˮ���л��ỹ����˵������
�����ϳ���˵�������Ӻβ�������ħ���ϴ��������ݹ��ص�����Ŀ�����������ܴ�������Լ�������ߵ��Ķ���������������ֽ���Ͳ���˭�����İ����ѻ���ɽ�Ŀ��һ������ȥ���ò����㵽�����˵��Ҫ����������ֽ�ˣ���ת��֮��ȦͲʽ����ֽ��ؿ������������ͬ��Լ����Ҫͬ������һ�����β�����Ϫ�ֳ�תһȦ��������ҡ�س��һ��Ⱥ��������Χ��ȥ����Ҫ���ʣ�Թ������ģ��������ֵģ������ٲ�������Ҫ���������Ůȥ���ҳԷ��ģ����÷��졣����Ҿ��ͷ�ô���Ȼ�ȥ�����Ƶ������Ⱥ������칫�ң����������һ���˵���˵��������������ʡ���һ��ë�ˣ�����ˣ��Ƥ����û�ã�ҪǮû�ã�Ҫ��һ������Ƹ�ת�����������ִ������ܽ�ȥ��˵��һ���¶����豸������ͷ��ծ�������ˣ�����Ǯ�����豸��ծ�������Ǹ����������ӣ���˵�˼Ұ������������ˣ��Ļ��ŵ�ס��ֻ������ҧ���������ϵ������������˼���ɶ��ѽɶ��ѽ��������һ������һ����Ѫ��ǹ����������˾������˵ص���ȥ�ˡ���
������ʵ�����¶��ƶ���Ҳ���ø���ţ�ֻ��û�ϳ���˵��������ϸ����������ȥ����ǰ�������ƶ����������ĬĬ�����̾���������˵�����˾���̫���ǿ���ֲ�ʶʱ����ʵ������ǿ������Ҳ�Ȳ���ֽ������Ҫ����������û���ۺ�ľ��������������Ź֣���ֻ��ֽ�����ҿ������ֹ�ҵ��û������������ˣ��ƶ������ȵؿ����ϳ�������Ȼ��Ҳ��������Ԥ�У���������Dz�Ը���ϣ����ϳ���һ���ӵ��������ʱ�������Dz���֮�ס�
��������ƶ������������ˡ��������˴���꣬���������ʮ�����Ѹ���Ϊ���Ṥҵ�ֵ�ԭ�ֹܾ֣�������λһ��������ŵ���������գ�ֻʣ�˸��ռ��ӵĶ�������dzŲ�����ά���˼�����Ҳ�ʹ���������ϳ��׳����ˡ��ƶ������ݺ��ڻ��ʦ������ı�˸�ְλ�������ȣ�һ���и���Ϫ�����IJ��£����źþ�ûȥ�Ƿ��ˣ�����ȡ���������˰�Ϫ�������£����β�������ȥ�������¡��뿪ʱ���β���Ů�˽�һ������ˮ�����ƶ������˵���������롣�ƶ����ο��������ᣬ���йɾ�ζ���ֵ��볧��ţ������ֽ����ַת��ת����������п����벻���Լ�Ϊ֮�ܶ���һ������ҵ����ͷ������ȦȦ��ҡͷ̾Ϣ֮�࣬��������ֽ�����ӻ������������ȥ����û�ҵ���
�������ߣ����Ľ��������ƺӣ������ߣ����ң�����֪�࣬���ˡ������쵼���ֹ�ְ���ʸִ�ý�����ʸ��ձ��硣
������ַ���Ĵ�ʡ��֦�����ʸִ�ý�����ʸ��ձ���
�����ʱࣺ617067
�����绰����0812��3381849��
�����ֻ���13882364982
(������Դ�������� �༭���﷽��)
�ؼ��ʣ�
������ţ�
��������
����Ҫ��
�����Ƽ�
������������ˮ���乩ů ���������������ů
�����ձ�Ѷ(��������ͨѶԱ����һ��쿺�������)˵�����й�ů�����˵�һӡ����뵽��ú���������ſƼ��ķ�չ�������õ���...[��ϸ]
��������Ȩ���������
�� ������ӭ����ý�塢�����硢Ӱ�ӹ�˾�Ȼ����뱾�����г��ڵ����ݺ�������ϵ��ʽ��027-88567716
�� �ڱ���ת������ý������Ϊ�����������Ϣ�������������������۵㡣�������ת�صĸ���漰���İ�Ȩ������Ȩ�����⣬�뾡���뱾����ϵ�����������չ�����ط��ɷ��澡�����ƴ�������ϵ��ʽ��027-88567711
�� ����ԭ��������Ϣ������ȷ�����Եı�ʶ��������������������"������"��Դ������ת�ط����Ǿ�����ԭ����������Ϣ����Ϊ�����������䷨�����ε�Ȩ����
�� �ڱ���BBS�Ϸ������ۣ�����������������Ӧ�����ԡ�������������ط��ɷ��档
�� ������ӭ����ý�塢�����硢Ӱ�ӹ�˾�Ȼ����뱾�����г��ڵ����ݺ�������ϵ��ʽ��027-88567716
�� �ڱ���ת������ý������Ϊ�����������Ϣ�������������������۵㡣�������ת�صĸ���漰���İ�Ȩ������Ȩ�����⣬�뾡���뱾����ϵ�����������չ�����ط��ɷ��澡�����ƴ�������ϵ��ʽ��027-88567711
�� ����ԭ��������Ϣ������ȷ�����Եı�ʶ��������������������"������"��Դ������ת�ط����Ǿ�����ԭ����������Ϣ����Ϊ�����������䷨�����ε�Ȩ����
�� �ڱ���BBS�Ϸ������ۣ�����������������Ӧ�����ԡ�������������ط��ɷ��档
对不起,您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已被删除!
10 秒之后将带您回到荆楚网首页
要闻推荐:
- · 30℃夏天来了
- · 荆州站北站收尾施工正酣
- · 湖北首座劳模工匠文化公园全面开放
- · 擦亮“蕲春艾灸师”劳务品牌
- · 来武汉,坠入花海